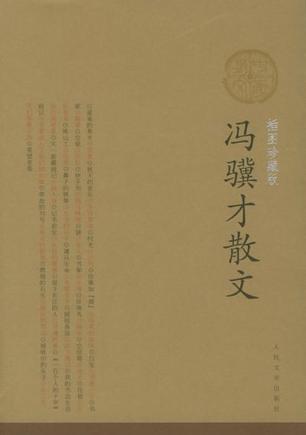敦煌追问/冯骥才分类文集
冯骥才
书摘
我把一九九六年称为自己的“沙漠年”。春天里我在尼罗河边的国王谷,踩着被毒日头烧红的沙砾,去寻找埋葬在那些热烘烘的大山深处的三千年以前的法老们的精灵。我汗流浃背地钻进那一个个画满古埃及人心中形象的阴冷的墓室,用我所熟悉的绘画语言去破译他们至高无上又神奇莫测的理想。然而,转过几个月后,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来到中国的大西北,同样踩着烫脚的大漠,由那条废弃千年的丝绸古道,一直走进和太阳一样灿烂夺目的敦煌石窟。
尽管一年里,我有幸看到的这两个沙漠上的画库,一东一西;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面之上。但它们全是地球先人心中的色彩、理想天国的景象,以及人类初始时代那种蓬勃清朗的精神。从中,我识辨出这人类文明最早几步清晰有力的足迹,然而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古埃及人表现的仅仅是他们自己;敦煌石窟却叫我发现多元的人类文化缤纷的因子,并惊异于它们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个整体的奇观。
使我获得这个美好感受的缘由是,我接受中央电视台和敦煌研究院等部门的邀请,为他们策划一部大型历史文化片的脚本而奔往敦煌。但当时我还没答应由我来执笔。此行更深的愿望,则是偿还自己远在少年就心怀不已的一个梦想。
我的邀请者之一——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孙曾田,是一位富于才气、缄默内向、主意过剩的人。他没有安排我们从兰州飞往敦煌,而是乘坐一辆快报废的破车,沿着当年周穆王、张骞、法显、隋炀帝以及张大千、常书鸿等都走过的漫长艰辛的河西走廊,一点点去往敦煌。现在想起来,这辆破车真是选择得好。惟有在这种破车的颠簸摇晃中,才能寻觅到当年那种古道牛车的感觉。而这条没有任何现代生活痕迹的千里之途真好比一条时光隧道。在不知不觉中我被引入了历史。
在敦煌,受到莫高窟巨大的美与文化的震撼之后,我又给这位导演拉到敦煌四外的大漠上,去造访一处处倾圮千年的古域。他肯定知道,对于我,历史的生命就是这些至今犹存的遗址;生动的历史精神依然在这些世间仅存的历史空问里闪闪发光。当我在那条通往玉门关——也是玄奘走过的丝绸古道上,被激动得连喊带叫时,我发现这位导演的眼睛异样的明亮。当时,还以为他和我一样被眼前这博大而辉煌的历史景象所降服。过后才明白,其实那是一种猎人捕到猎物时的目光。我已经如醉如痴地中了他甑圈套。说服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叫他深深感动。于是我主动伸出手接过这一写作的使命。敦煌已经把我对历史、文化、佛教帑艺术钓想像疯猛逝.燃烧起来。任何作家在创作激情到来时,都是妄自尊大。那时我甚至狂妄地认为,这件事非我莫属!
在返回天津后的两个月里,我把一切都思考成熟,写出提纲,这便是收在本书最后部分的“附录”。也许由于受到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的启发——他主张拍一部“空前绝后”的巨片。因而我从最初构想时就拒绝以往的电视片所采用的介绍性方式。史诗性是我写作的起点,也是竖着目标的终点。放眼敦煌,线索错综复杂,但有五条大的历史线索,犹如地图上走势清晰的山脉:即中西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佛教东渐史、北方史、中古史和敦煌石窟艺术史。其中任何一条线索都可以作为主线,但是任何一条线索也无法将敦煌博大恢弘的精神内涵包容起来。我决定将所有整块历史内容全部打碎,按照不同的特点和独自的思想命题,重新组合,构成一个个动人的形象的历史空间。这种写法,近于文学创作。敦煌的素材浩如烟海,打碎的素材庞杂无边。当我进入写作后,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的大山压在自己的脊背上。将近一年的写作期间,我常常会听到自己的脊梁骨嘎嘎作响。
大概我为自己的创作想像迷惑过深,轻易答应来写,一旦动笔,便尝到陈寅恪先生所谓“敦煌学”的浩瀚与艰深。凡世上成为“学”之学问,必定是博大精深、逻辑严密、内在价值无算。仅仅是自成体系,难以成“学”。国内外几代敦煌学者,都是在学术苦海中倾尽一生,最终不过磨出小珠一二而已。而言必有证,几乎又成了敦煌学苛刻的诀要。有多少空间,由得我来纵横捭阖,恣意挥洒?行笔之间,时时感到笔尖下是黑黑的学问的陷阱,何况单是内涵繁复深奥的壁画就有四万五千平方米之巨!即使今日脱稿罢笔,仍不敢说自己已经进入了“敦煌学”,却明白敦煌是我至今遇到的一个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它不仅是一切人文,无所不包;更由于它面对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所表现出的宽容、亲和、慷慨,以及主动——主动地吸取和主动地融合。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最积极、最有益于未来的主题也在其中。
正是由于它如此的庞大严谨,无不重要,疏漏不得,便常常压得我透不过气。这期间,我竟被逼得逃逸出来半个多月,几乎一挥而就地写了另一部全然不同、属于未来、天马行空式的小说《末日夏娃》。用一部小说的写作作为心灵的调节乃至喘息,是我前所未有的一次体验。其间奇异的感受只有另文表述。
以往电视片脚本,多是概说内容,勾勒紧要。然而对于敦煌,由于它本身高度的学术要求与内容的缜密性所决定,必须表达详尽精确,巨细无遗。同时,按照我本人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还要阐明思想发现,构筑独有的艺术空间。这样便给自己设置一道难题——写一种样式上全新的电视片脚本。即将复原性历史情节的画面刻画、实拍内容的确凿描述、闪光的思想提示,与文学性的解说词,构筑成为一个整体。脚本就是剧本,它是提供给导演工作时使用的。它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导演的再创造。它的语言,首先是可以转变为镜头语言的。当然,它又可供阅读,这是由于我努力使脚本散文化。但读者阅读时需要有个前提,即运用自己丰富的镜头想像。而运用想像的阅读才是真正和幸福的阅读。
大约一个月前,我写完这脚本时,将手中的笔扔在桌上。人在书房中间的地上独坐许久。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一年来塞满躯体的广博浩瀚的素材,此刻连同身上的血肉精神,全搬到那一大堆稿纸上。剩给自己的,不是满足,亦非失落,而是一种美好无比的空洞感……然后,过些天,渐渐才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一点点回到身上。对于敦煌的写作,使我受益匪浅,甚至会终生受益。我陡然感到身上有一种文化上的强大。
你只要为它去做,得到的就一定比付出的多得多。这便是敦煌。还有,只有真正写过敦煌,才会最深刻地感受到敦煌。
这时,我才想到感谢邀请我来写敦煌的中央电视台和敦煌研究院,包括那个又有才气又有主意的本片导演孙曾田。如果世界还有什么像敦煌这样文化的圈套,我一定会再钻进去。
我也要感谢唐史专家黄新亚、敦煌学者刘玉权等同志给我有力的帮助,他们渊博的才识使我在一如大漠的敦煌中没有迷失,而是快捷又准确地抵达了我的目的地。
我还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是他们独具的出版眼光,将我这部作品以完整的电视文学剧本的形式问世,并因之使我蕴藏其问的历史观和艺术史观奉献于社会。
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天津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