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精神
1935年,当时已被纳粹封口的哲学家胡塞尔预言: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要么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他得出结论,欧洲面临最大的威胁,是自我懈怠。 作为一个精神国度,欧洲在“哲学精神”中究竟应该恢复些什么?几十年来的欧洲问题——关乎它的意义和职责,从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的知识分子们中间传播开来。为了探索欧洲建立的意义与价值,许多中欧知识分子贡献出了他们的作品、智慧甚至生命。 本书主述的三位思想家——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捷克哲学家雅恩•帕托什卡,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向我们证实,哲学欧洲是存在的,人们坚持去探索欧洲的意义,探究它的终极精神目标及意义之所在。 米沃什、帕托斯卡和毕波,恰恰是在他们身陷黑暗期间,给我们带来了最重要的哲学探索,改变我们对欧洲、世界、民主诉求,乃至自身的看法。他们都可以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良心之列。 这个美好的精神团体,还包括卡夫卡、伊姆雷·凯尔泰斯、柯斯勒、米兰·昆德拉、穆齐尔、胡塞尔、汉娜·阿伦特、桑多·马芮以及齐格蒙特·鲍曼……本书重现了他们关于欧洲文明道德基础的讨论。通过追溯,被湮没的欧洲文化将重新出现,我们亦据此得出启示:欧洲的再次统一不应以人性与民主的消亡为代价。 欧洲首先是一个精神国度,或者说一些精神的家园,它的重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它的优越性存在于新的“政治道德”之中,跨越了国境。 ——捷尔吉•康拉德 (匈牙利作家) 有了米沃什、帕托斯卡和毕波,中欧,甚至整个欧洲,或许都能寻找到最完整的关于哲学、道德和政治的表达方式。这便是未来思想欧洲的开端。 ——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 -

第二空间
《第二空间》是米沃什晚年最后一本诗集,在他去世那年出版,写作时诗人已逾九十岁。如同诸多伟大的作家高龄时一样,面临大限,此时他们往往从宗教的角度寻找“生死”这个永恒问题的答案,是一生寻遍之后的唯一归宿吗?时间的意义、生命的真相,乃至神学的真伪,等等,一个老人的思考,远离了尘世的纷扰,而与终极终极世界更相接近,安静,广阔,深邃,悲悯。 米沃什在国内已经享有深远的影响,有众多崇拜者,这本诗集是首席推出,当能引起读者关注。 -

攻心記
-

冻结时期的诗篇
切斯瓦夫•米沃什,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之一,以其无可匹敌的与优雅,定义了他所属时代的悲剧与美。他的诗歌,无论是描述他在波兰度过的少年时代、战乱中华沙的悲痛或对信仰的追寻,都令人啧啧称奇、惊叹不已,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平凡人生的个体性。诗歌对死亡、战争、爱与信念的探索扣人心弦,震动人心并为之深思低回: “在这片大地上存在过,其本身已远非任何语言可以形容。”
《米沃什诗集》汇集诗人1931年至2001年间几乎所有的诗作,分四卷呈现。本书为《冻结时期的诗篇:米沃什诗集》,收录米沃什诗作56首,来自《冻结时期的诗篇》(1933)、《三个冬天》(1936)、《拯救》(1945)白昼之光(1953)、《诗论》(1957)和《波庇尔王及其他》(1962)。多为长诗,既有色彩浓郁的抒情与描写,也有激烈愤慨的嘲讽与批判。在此期间,米沃什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写下《菲奥里广场》等名篇。
《着魔的古乔:米沃什诗集》本卷收录米沃什诗作73首,来自《着魔的古乔》(1965)、《没有名字的城》(1969)、《散诗》(1954—1969)、《太阳何处升起何处降落》(1974)和《珍珠颂》(1981)。多为诗人移居美国后的创作,部分作品透露出他定居新大陆的幸福感,但仍不乏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故土追忆:米沃什诗集》本卷收录米沃什诗作87首,来自《故土追忆》(1986)、《纪事》(1985-1987)和《彼岸》(1991)。诗人追忆已逝的人和难以涉足的故土,沉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但“还是学不会妥帖叙事,平心静气”。
《面对大河:米沃什诗集》本卷收录米沃什诗作120首,来自《面对大河》(1995)、《路边的小狗》(1998)和《这》(2000)。诗歌包了与其他人士的往来对话,对人世的描述冷峻,字里行间热血依旧,延续了对善与恶、真实与自由的探讨。诗人将个人经验和历史视角融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启示性的洞察力。
-

被禁錮的心靈
1930年代至40年代,米沃什歷經波蘭屢受侵略、瓜分,二戰期間,目睹華沙在納粹德國的破壞下變成了廢墟。米沃什關切著斯土斯民的命運,他從反納粹戰爭開始就積極參加了波蘭的抵抗運動,在淪陷的華沙與法西斯德國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二戰結束後,波蘭雖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立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米沃什亦曾任波蘭駐美使館和駐法使館的文化參贊,然而他認為政府當局要求藝術家作品中「革命」服務,侵犯了作家特有的職責。於是米沃什在1951年初要求在法國政治避難,從此自我流放到西方。 米沃什在法國流亡了十年,1960移居美國,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任教。1970年加入美國籍。 在米沃什三十多年的流亡中,過的「是一種與城市大眾隔離的生活」。他自稱是「一個孤獨的人,過著隱居的生活」,並表示「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簡直墜入了深淵。」 1980年米沃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接受美國《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採訪時曾說:「獲獎給我帶來了讀者和困擾。我擔心自己的作品會遭到曲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寧願不要讀者」。 1989年後,米沃什結束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波蘭,在古城克拉科夫定居直到2004年8月辭世。儘管米沃什的一生漂泊不定,並精通多種語言,然而他始終堅持用其家族從16世紀起就使用的波蘭語寫作,儘管米沃什過去的出生地已被畫為今天的立陶宛,他仍然把波蘭視為祖國。本書是米沃什政論思想的奠基與成名之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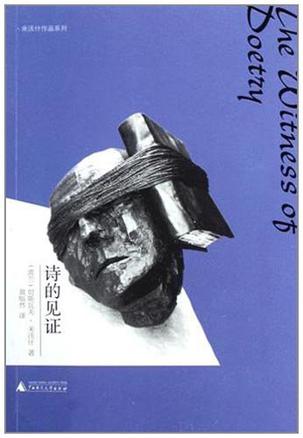
诗的见证
本书乃米沃什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约所做的六次讲演的结集。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见证功能的阐释极其精辟。借助这本小册子,米沃什论述了诗歌之于时代的重要性。米氏所言并非老生常谈,他提醒世人关注的恰恰是诗歌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为这一思考维度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指向。 米沃什向来直接,甚至简单。他有能力把诗歌的快乐归还给普通读者,而在他的散文中,如同在本书中,他则使你怀疑我们时代知识阶层最大的罪孽,是害怕明显的东西。 ──《名利场》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以某种平静、卓越的才智说话,这使得他所作(关于诗歌)的辩护……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部经典。 ──《星期六评论》 米沃什这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诗的见证》以其浓缩和简洁阐述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一把了解米沃什诗学历史哲学、哲学和美学的钥匙。当然,米沃什全部著作提供了对二十世纪困境的最深刻反应之一。他反对各种一般见识,这些见识认为我们文明是没有前景的,而文化的异化则是可无逆转的事实。他的反对,对他的波兰读者来说似乎可能更自然。毕竟,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当代诗歌不止一次地证明它是社会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它发挥见证现实、抵抗压迫和成为希望来源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抽象原理,而是很多人具体和亲身的经验。 ──《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