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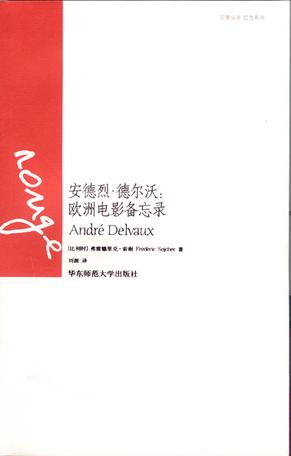
安德烈·德尔沃:欧洲电影备忘录
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太多强烈的矛盾,激进的民族主义打算在经济上灭亡或者排挤所谓欧洲电影,逼着我们要坚持电影的欧洲特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反思越多,就越感觉到欧洲这个概念很自然,就像我们生活的气候是欧洲大陆的普遍气候这个事实一样自然。我已经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和欧洲一体化连在一起的…… 有些导演在生活和电影里只谈他们自己。自传电影很沉闷,自命不凡,带着难以忍受的无趣。这个星球上的六十亿人都差不多,不可能用这些东西来吸引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关心的是作品,而不是创作的人。……我们不能够区分写作的作家、拍摄的导演和银幕上看到的演员。然而,我们在实际上是远离自传体的。我们自以为知道谁是伍迪·艾伦,但事实上,伍迪·艾伦的叙述世界却处于持续不断的(再)创作之中。 -

至爱手记
演员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时而强悍,时而脆弱,时而阴柔,时而阳刚,时而慷慨,时而吝啬。处于一种持久的不平衡状态,唯有独脚踩在自身理性的边缘舞蹈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怎样才能理解这同一个载体上所有不同的展现面,而不把他当成疯子7显然唯有接受演员本身的模样:变色龙为了生存需要变幻颜色。为了重新找到自我、发现自我,需要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旅行。我们是演员,因为这是生命的根本。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历程,字里行间的那种谨慎,完全体现了他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读着这些回忆的篇章,才发现他的举重若轻绝非假装,而正是战后那个时代的典型。他们徘徊在圣 日耳曼大道上,他们跳啊,他们唱啊——正是从那一代年轻人中,诞生了新浪潮。 本书收录了卡塞尔的28篇文章,回忆了作者本人与让•雷诺阿、阿贝尔•冈斯、梅尔维尔、德•布劳卡等法国电影导演大师,以及弗雷德•阿斯泰尔、卡拉斯、金凯利等演艺明星的合作经历和相识过程。卡塞尔以亲切而生动的文字,娓娓述说着这些20世纪欧美戏剧和电影界的传奇人物与传奇故事。 -

关于电影
科克托与查理·卓别林同时出生于1889年,所不同的是,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平民的家庭,而科克托则降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家庭,自幼便浸润于上流社会的氛围中。六岁的时候,科克托便观看了卢米埃尔兄弟早期的影片《水浇园斗等,并接触到了戏剧和马戏。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开枪自杀。父亲的死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魔咒,悲剧主题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循环出现,死亡与血追随着他的作品,如《诗人之血》、《双头鹰》、《永恒的回归》、《俄耳甫斯的遗嘱》等。极具艺术修养的外祖父每个周末都带他去听音乐会,他因此发现了贝多芬、李斯特、瓦格纳等,音乐的熏陶对他一生的创造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他涉足的艺术领域甚广,真正留下来的,或许正如弗朗索瓦·佩里耶所说,“还是他的电影”。他的艺术声誉主要来自于电影,他甚至被认为是法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不仅与雷诺阿、布莱松等人齐名,更作为不受教条约束、进行自由创作的艺术家典型,得到戈达尔、特吕弗、雷乃、德米等后来的新浪潮年轻导演们的仰慕。 其实,科克托直到1927年才尝试电影拍摄,而这部与一些朋友一起拍摄的、题为《让·科克托拍电影》的16毫米影片已无处找寻。当诺阿耶家族在1929年底建议他拍摄一部动画片的时候,可以说,他对电影拍摄知之甚少。然而,他很快在电影里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新空间、新语言,最初的动画片最终在1930年变成了传世先锋派影片《诗人之血》。 如果说令超现实主义者们反感的《诗人之血》成了心理学家和电影爱好者感兴趣的典型,那么1943年拍摄的《永恒的回归》终于为他赢得了观众,这部以中世纪特里斯唐和伊泽的传说为原型的现代故事,重新燃起了他对电影的激情。而大获成功的《美女与野兽》则可以说是幻梦剧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影片。 科克托将电影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他借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俄耳甫斯之名,唱出了诗人之歌《俄耳甫斯》和《俄耳甫斯的遗嘱》。他说:“《俄耳甫斯》曾经是我的‘总和’,我将我全部的生活都放了进去。”而“《俄耳甫斯的遗嘱》将是我对电影的告别”,“将是人们在船或火车消失之前挥动的手帕”。 于科克托而言,电影应该是以诗的形式来探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他对于电影的独到见解,在《关于电影》一书里,有着详尽的论述。他向来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将电影称为第十位缪斯,虽然年轻,但也应像其他缪斯一样拥有高贵的身份。他多次引用穆索斯基临死时惊人的预言:“未来的艺术将是那些会动的雕像。”会动的雕像即电影,电影即艺术。他厌恶以商业为目的的电影,急功近利使电影误解它作为缪斯的神圣使命。他崇尚黑白电影,彩色就像“吸引昆虫的假花”,将淡化电影的神话色彩,使电影里会动的雕像接近现实,变得庸俗。 科克托的影片通常曲高和寡,这也许与他对电影的艺术要求吻合。他希望电影能跟其他缪斯一样,做一只母螳螂,吞噬它爱的人,让爱人的作品代替爱人活着。伟大的艺术品通常在艺术家死后获得价值。科克托影片的价值,在电影史里才充分显现出来。应该不要忘记的是,科克托还为众多法国著名导演编写了剧本,其中就有布莱松的杰作《布洛涅树林里的女人们》。因此,这位诗人电影艺术家在法国电影里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

印象派画家的日常生活
本书系“巴黎丛书”红色系列之一本。 “印象派”近乎昙花一现的创作活动持续了不足20年,即从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到1883年马奈辞世的那段时期。 今天的人们看到印象派作品居然价值连城时,热衷道听途说就往往会使人们过分夸大印象派画家在其事业初期所经历的各个方面的困难。本书既不讲述印象派的历史,亦非印象派画家的传记集,其宗旨在于再现那些以落选者沙龙为起点、开始向始终受到官方保护的没落学院派发起进攻的画家的生活和创作状态。 印象派画家的历史往往被蒙上传奇的面纱,致使真实扭曲变形。将印象派画家从传说中脱离出来、还他们于真实的日常生活之中,使读者能够以全新的角度评价和欣赏法国艺术史上那个独特的时期,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

卢瓦河畔的午餐
造访一位敬仰已久的人,宛如一次朝圣。《卢瓦河畔的午餐》就是记录这样一次“朝圣”的几个小时。作者造访的主人,就是法国著名小说家朱利安·格拉克。当年,他曾因获龚古尔大奖却拒受而掀起很大的风波。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戈古堡》被布勒东赞誉为其所“梦想的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这部作品亦为王道乾先生的翻译遗稿。用一本书记录几个小时的“午餐”,有爱丽舍宫,有拉斐尔前派画家,有罗兰·巴特,有阿拉贡,乃至伽利玛夫妇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两个人的对话,貌似漫无边际,却在不经意中拉开了20世纪中叶的巴黎文化风景。全书只有简单的叙事,但平淡的言语里不时闪现思想的睿智之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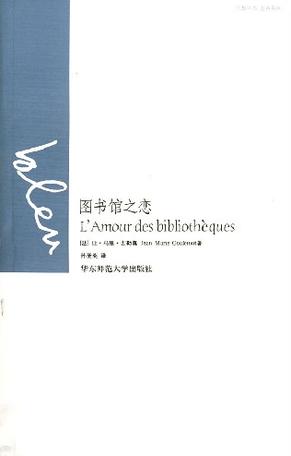
图书馆之恋
在常去的图书馆里,我们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阅读。阅读常常让我们置身于一种缺席的状态,一种精神上的别处,比周围的世界更加真实。阅读时我们忘记了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或愉快或不以为然的目光,也逐渐忘却了身体的束缚。被书吸引的读者完全沉醉其中,就像一个嗜睡的人一样任凭身体做出一些冒失的举动。沉浸在阅读中的读者自己毫无察觉就会做鬼脸,抓头皮,叹气,傻笑,皱眉,有时还会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技巧挖鼻孔,掏耳朵。我的本意并不是谴责这种随便的行为,人们可以将类似行为视为一种重获的自由,或者正相反,一种不合时宜地追求自由的结果。 我到图书馆进行真正工作上的写作。如果说有时我会对自己当了四十年的教师感到遗憾,而且我今天可能又比昨天更后悔,那么我却从未质疑过在图书馆度过的那些小时、天、星期、月,还有年。作为对这些罗列式比较的结束,我可以说我认识的图书馆绝对比我认识的女人多。 长久以来,我都乐于相信黎塞留路的图书馆是一个理想之地,不会受到世间沧桑和偶然事件的影响,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能够被它接纳,我感到骄傲和幸福。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就是天堂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