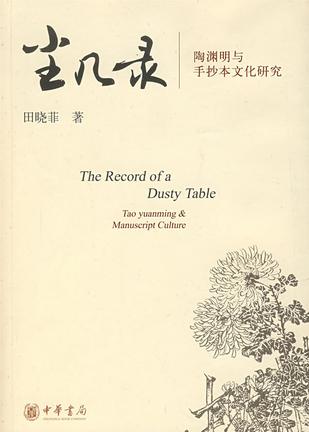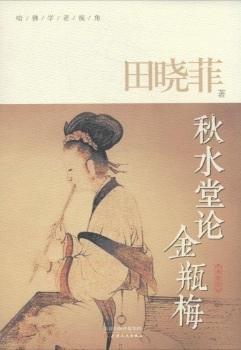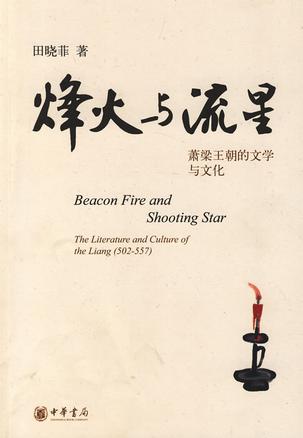“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
田晓菲 编译
关于本书
惭愧,我不懂希腊文。这本书里的译文,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老柏拉图”说: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像之影像。用在本书,恰好适合。
好在萨福的英译本历代层出不穷,仅二十世纪就有十数种。我参考的各种译本,详见书后开列目录。其中特别以娄伯(Loeb,或译勒布)经典文丛的坎贝尔(D.A.Campbell)译本和安・卡尔森(Ann Carson)2002年出版的译本为底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本子作为蓝本,是因为他们的翻译都是尽量依照原文,并不像威利斯伯恩斯通或者玛丽巴纳德的译本那样自行补缺并进行“文学加工”(在个别残诗的译者注里,我特意附上他们的译文,以便读者进行比较),因此,可以更好地反映萨福的“原貌”,除了文学价值之外,也有学术价值。
卡尔森既是学者(她现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墨吉尔大学教授古希腊罗马文学),又是诗人和作家,她的个人作品《红之自传》曾被《纽约时报书评》选为“当年最值得注意的书”(1998),苏珊・桑塔格称之为“令人迷醉的创举”。她的作品得力于古希腊文学,而她对萨福别具一格的翻译和笺注也格外吸引人。坎贝尔把萨福学者所作的“推测性填空”都放在括号里面,卡尔森则甚至在译文里用方括弧的形式保存芦纸残缺文本的风貌。她在前言里说:她相信这些方括弧暗示了充满张力的空白。这虽然未免让人想到佛班克在小说《虚荣》里的调侃,但萨福遗诗的残缺,文学史的一次偶然性事故,的确部分地构成了它经久不息的魅力,留给后人无穷的空间,在各种意义上,各个层次上,重写萨福。
于是,遵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在诗的空缺处以□□□示意――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地浪漫高深,而是带一丝微笑,把它当成一种精致的游戏。我希望读者也能如是看待之。
在安排这样顺序时,我依照了娄伯经典文丛里的次序。虽然诗前编号是本书自己的,但我在诗后括弧中一一注明娄伯编号,因为那是萨福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序号,便于讨论时引用和查找。
本书不是萨福残诗的全译,大约只是一半而已。选择的标准比较主观,但我还是尽量选取(一)著名的篇章;(二)在残诗坚相对而言稍微成意思的篇章(因此,只有一个词――譬如“芹菜”――抑或只有三五词的断简,就往往忍痛割爱了)。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辑收诗101首,是学者们公认萨福所作的歌诗;第二辑收诗12首,是学者们持怀疑意见的萨福歌诗;第三辑选录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它们或以萨福为题材,或从萨福歌诗中汲取灵感和典故。第三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欧美文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当代文学作品,充满对文学过去的回声。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唤起我们读者的注意。1944年,周作人在《文艺复兴之梦》中说:“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务新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对“新”之来源不其了了,则如此去了解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总是难免皮毛。
近年颇有谈“外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悦者。抛除其种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谈,多半由于不悦者看来,影响便等于依存。其实不然。一来,凡本性喜欢依存,不喜创造者,就算只读本国经典也还是要“依存”的;二来,我觉得就是以“外国文学的影响”立论,也还是狭隘了一点。引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作家郎古斯写在《达弗尼斯和克洛伊》前言里的一句话以作结:
我写了这个故事,一共分为四节,作为对
爱神厄洛斯、山林仙女、还有大神潘的供养,
也作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拥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