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随着报纸、书商的崛起和阅读大众的出现,文学日益分化为艺术和商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这在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引发了关于艺术与通俗文化问题的争论。在本书中,作者不但系统梳理了历史上通俗文化论战中交替出现的重要观点,而且对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重要命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炼出了争论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并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对艺术性和非艺术性文学的社会角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分析方法。本书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大众传播条件下出现的文学转型和通俗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洛文塔尔探讨大众文化的顶点是1961年出版的选集《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马丁•杰伊(Martin Jay) “洛文塔尔的作品很容易与卢卡奇(Lukács)、克拉考尔(Kracauer)和阿多诺(Adorno)对艺术的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恰好是这些细节揭示了洛文塔尔的独特性,正是洛文塔尔解码了作为‘过去几个世纪社会化模式讣告’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证词。”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称赞洛文塔尔的研究(指本书第四章)是欧洲理论姿态和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相结合的罕有的成功范例之一。” ——格特鲁德•罗宾逊(Gertrude J. Robins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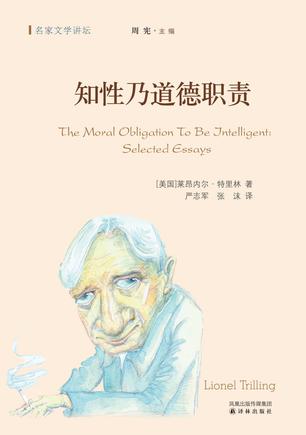
知性乃道德职责
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观念的缩影,特里林采用了一条更宽广的途径——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来应对当时的新批评主流。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文章,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他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崇拜它,尊 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具有重要影响。 -

文化批评往何处去
文化批评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它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政治的公民行为;它剖析、评价与“共同的善”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和群体价值,难免会触及“不方便”的政治敏感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撤离了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政治敏感议题,丧失了文化批评的公共政治锋芒,变成一种精致而无目的的游戏,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 叩问“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就需要重申文化批评的公民政治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传统。这样的文化批评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宪政民主建设所必不可少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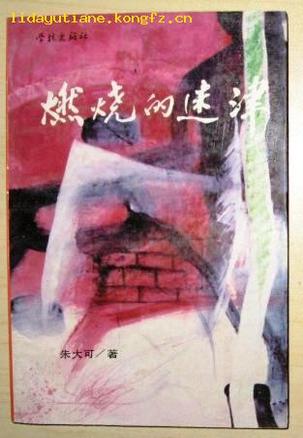
燃烧的迷津
-

话语的闪电
机智的隐喻和精辟的警句层出不穷,体现了作者罕见的语言智慧:“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尤其是朱大可的时政批评和神话阐释学,颇具“杀伤力”,因而赢得了“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独特的话语风格,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挑战。该书汇聚了朱大可的大部分文化批评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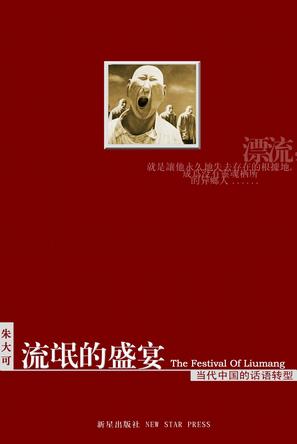
流氓的盛宴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