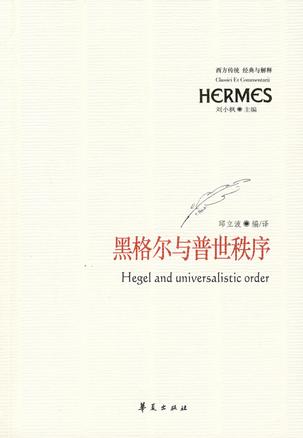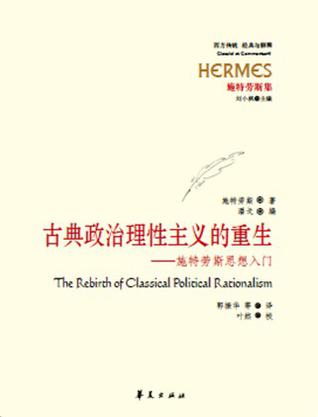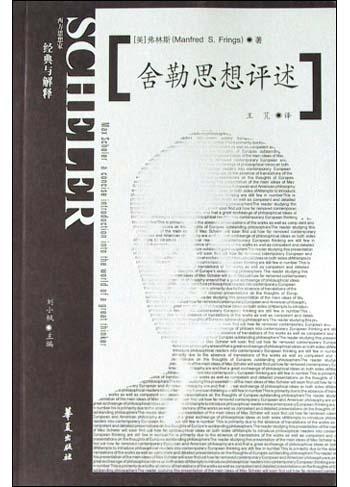柏拉图的三部曲
【美】克莱因
克莱因看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的大背景下,所以,“什么(或者谁)是哲学家?”的问题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可以说,三部曲也构成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克莱因认为,理解三部曲的关键是位于中间的《智者》篇。根据克莱因的阐释,《智者》在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总是会有哲人与智者,可以说,哲人与智者一起,正是一个未定之二,所以,关于哲人、智者与政治家,柏拉图不需要另外写一篇《哲学家》。克莱因的结论是,正如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两天之中,哲人、智者与政治家这三者仅仅是二。
目录
中译本前言
第一篇 导论
第二篇 寻找智慧之师与发现爱智慧者
1. 开头
2. 为逮住智者所做的头四个“分析”
3. 第五个分析
4. 总结与“修正”
5. 智者之为影像制造者。“影像”的意义
6. “不-是者”的问题
7. 客人的真面目
8. “是”的问题的产生方式
9. “提坦神”与“奥林匹亚神”的意见
10.“两者偕”的意思
11. 诸理型的混合、哲学家的出现
12. 言说诸最普泛理型的困难
13. “不-是”作为“异”
14. 为什么如此频繁地用“皆”字?
15. 言语与思想中的错误
16. 最后一次分析
第三篇 种类型的错误
1. 开头
2. 知道意味着感觉吗?
3. 忒奥多洛的进步
4. 知识不是感觉
5. 知识是正确的意见吗?
6. 知识是正确意见加一个说法吗?
7. 尾声
第四篇寻找政治家
1. 开头
2. “竖向的”尝试
3. “平行的”尝试
4. Ἀπόδειξις[现出]与 παράδειγμα[范例]
5.在言语中编织事实上的编织
6. 适当尺度与准确本身
7. 政治家技艺中的协助原因
8. 众所周知的政体及其弱点
9. 法律及其不足
10. 对各种政体及其方式的最后考察
11. 真正的政治家如何编织
译后记
中译本前言
——雅可布•克莱因和他的《柏拉图的三部曲》
雅可布•克莱因(Jacob Klein,1899-1978),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柏拉图阐释者。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终生挚友,他可能是复兴施特劳斯所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之一。
克莱因是俄国裔的犹太人,1899年3月3日生于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Liepāja,在德语中叫Libau),他的名字在拉脱维亚语中就叫Jēkabs Kleins。他所受的学校教育一开始是在利佩茨克(Lipetsk,俄罗斯西部利佩茨克州首府。位于沃罗涅日(Voronezh)河两岸),接着在布鲁塞尔(1912-1914),1917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实科中学(Friedrichs Realgymnasium),然后,他在柏林和马堡大学学习哲学、物理学和数学。1922年,他在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指导下在马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随后的年月里,他继续在柏林和马堡学习、研究。他的著作《希腊的数学思想与代数学的起源》的第一部分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若不是德国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这本书本来会让他在1932年10月获得柏林大学的教职。1934-1935年,他任布拉格大学的数学史教授,1935-1937年,他是门德尔松人文科学促进基金会(Moses Mendelssohn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研究员。1938年,克莱因到了美国,不久就在位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开始执教,一直到他1978年7月16日在此逝世。 1949-1958年,他出任该学院院长,在打造学院的经典名著课程(the great books curriculum)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
克莱因生前出版的著作有三部,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著名的《希腊的数学思想与代数学的起源》, 其论题,准确地说,是关于希腊数学思想与现代代数学的起源,它冲决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见洞穴,力图以古人的眼光理解古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希腊算学(logistic)与数学(arithmetic)思想与希腊本体论的关联,并探讨希腊数学思想在近代数科学中的复兴与嬗变,特别是符号代数在16-17世纪的发展,指明了在数的概念上存在的古今巨变,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变化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这是他研究柏拉图的首个产物,施特劳斯说,“在我看来,在思想史的整个领域,至少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该著作无与伦比。” 这并非朋友间的过誉之辞,一些对比研究克莱因与胡塞尔(特别是其《危机》)的二手文献确乎显明,关于现代性的看法,这位后学在视野上超过了他的前辈。 在克莱因生前发表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论文中,有一篇“现象学与科学史” 就发表在胡塞尔纪念文集中,这篇文献现在收入其《演讲与论文集》中。第二本书是《柏拉图〈美诺〉疏解》, 发表于1965年,前一年,施特劳斯刚刚出版了堪称其诠释学范本的《城邦与人》,克莱因也在自己的书中阐述了细读柏拉图的诠释学原则(第3-31页)。他的疏解是对《美诺》的逐段解读,它把我们现代读者带进到柏拉图对话录的戏剧情景,回答了“美诺是谁”的问题:美诺的无知(amathia)正在于他拥有极好的记忆而拒绝学习,美诺停留在城邦通常的意见里而拒绝追求知识,于是,作为“某种知识”的美德在美诺身上实际上是不可教的。重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性,对理解柏拉图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克莱因的著作堪称典范,在当时实为空谷足音,施特劳斯把这一重要发现归功于克莱因,伽达默尔则称自己也该分一杯羹。 1966年春季,施特劳斯讲柏拉图的《美诺》,就用了克莱因的疏解作教材,没有第二个同时代的作家能在施特劳斯这里享有如此殊荣。克莱因的第三本书就是现在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三部曲》。 1985年,其门人编辑出版了克莱因的《演讲与论文集》, 这本文集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多识。他的著述目录,还可见于Murley所编的施特劳斯派书目。 若要得到他更详尽的文献,现在便只能寻求圣约翰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的“克莱因文章书信收藏”(the collected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cob Klein)了。
1977年,施特劳斯已经逝世四年,整个施特劳斯学派在学术界还默默无闻,克莱因出版了他的《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在本书一开始,他简洁而优雅地重申了他阐释柏拉图对话录的原则。正如 Lachterman在他非常精彩的评论文章 中所说,这些原则所遵循的范式“游离”于英语世界主流的柏拉图研究范式。这两个范式是“对手”,克莱因的研究对后者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可以理解,它实际上是对主流学界的冒犯。根据Lachterman的总结,主流的柏拉图学界——或是来自广义的“分析哲学”传统,或是偏重语文学的“发展”研究——有共同的范式:主要关注对话录中适合做形式-技术分析的“论证”内容;论题来自当今哲学构造的主题和结论,并据此检验柏拉图的得失;把柏拉图对话录分成早、中、晚期,以一种目的论倾向把柏拉图的思想看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即,中期理念论的内在危机迫使柏拉图日益趋近于现代哲学所熟悉的逻辑分析观念。我们可以说,这些套路实质是以现代哲学的观念透视柏拉图,为了“比柏拉图自己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康德),只见柏拉图作品的“哲学”方面,不见其“诗”的方面,于是,这一范式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视柏拉图对话的文学特征,忽视其中的论证在整个戏剧情节中的位置和作用,它剥掉对话中所谓“非本质的空话”(G. Vlastos),直指其论证的核心,像黑格尔明确说的,对话应该被转化成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文。克莱因的范式与此刚好相反,它要求我们的五官与心灵向柏拉图戏剧中的“言语”与“行动”敞开,不要太过匆忙地相信某个角色的台词,把某个人物(哪怕苏格拉底)当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要求我们作为听众参与其中,参与其对话(辩证法)的历程;要求我们重视戏剧中严肃与玩笑的“姊妹”相连(与苏格拉底的特有反讽相关),或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对话是悲剧与喜剧的结合;它要求我们认识到柏拉图对话录像一个“宇宙”,其中的每一要素都具有它特定的意义,而某些细节可能比冗长的言语更加重要;它要求我们在理解柏拉图思想的所谓发展之前,就一篇对话本身,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克莱因(或者施特劳斯)的发明或首创,我们可以在很多古代作家的洞见、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注释实践中发现其传统,在现代仍然为施莱尔马赫所重申过。为了理解并解释柏拉图,它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到胡塞尔指出的现代哲学诸“自明”概念背后的历史“沉积”,力求回到希腊概念本身的意义上;它要求我们的哲学阐释遵循哲学活动的上升与下降历程,首先不是从既有的哲学理论出发,而是要从海德格尔所谓日常生活的“实际性”出发,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从城邦的意见出发,这一历程是柏拉图对话录无与伦比地展示给我们的,以致“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与阅读柏拉图密不可分。这样的阅读首先正视一个困难:我们很难说柏拉图的哪些文本明确表述了他的思想(正像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之于其思想),相反,柏拉图倒是明明贬低写出来的文字(《斐德若》274c以下),并说关于最高事物的知识不能写出来(《第七封信》341c-e),这样,我们似乎根本没有达到柏拉图真正学说的可靠门径,以致有必要寻求柏拉图“未成文的学说”,或者说,“隐微的”(esoteric)学说。
上述所有要点,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施特劳斯所分享。 看来确实可以说,克莱因与施特劳斯同为复兴“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这两位大师的区别在哪里呢?
克莱因看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的大背景下,所以,“什么(或者谁)是哲学家?”的问题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可以说,三部曲也构成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一种哲学上的辩护。 克莱因认为,理解三部曲的关键是位于中间的《智者》篇,它的主题是“对智者(智慧教师)的寻求”,其核心理论,当然是其中的存在论:对非-存在的存在性,以及种(克莱因把它们等同于理念)的相互交流的论述。只有让非-存在具有某种存在性,才能说明虚假意见与言辞的可能性,从而说明智者的存在;只有让某些种之间可以相互混合、交流,才可能进行清晰的思想与言谈,从而有哲学家。克莱因的阐释,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基于对细节的重视, 通过重述对话情节,他让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在对话中反复提及两者“皆”或“偕”,其意在提醒我们:1)存在是动与静两者皆一起,而非两者之外的第三者,根据克莱因,理念数系列的第一个就是“理念数二”;2)非-存在作为“异”,总是异于某物(存在),“异”体现了“未定之二”;3)“同”总是与异成对出现,它所对应的则是“一”。总之,在克莱因看来,《智者》集中展示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理念与数紧密相连,理念与数的两个最高本原是“一”和“未定之二”(正如亚里士多德准确叙述的那样)。根据克莱因的阐释,《智者》在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总是会有哲人与智者,可以说,哲人与智者一起,正是一个未定之二,所以,关于哲人、智者与政治家,柏拉图不需要另外写一篇《哲学家》。克莱因的结论是,正如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两天之中,哲人、智者与政治家这三者仅仅是二。
对克莱因阐发的这种柏拉图的隐微学说或本体论,施特劳斯大概也会赞同,尽管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从未见到这样的内容。 在这里面,未定之二尤其让人感兴趣,如同伽达默尔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对柏拉图戏剧特性的重新发现扩展到政治理论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阐发的隐微的本体论贯彻到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中,施特劳斯的主题——不管是“耶路撒冷与雅典”以及相应的古代与现代、哲学与诗歌之争,还是如克莱因所说的上帝与政治——无不体现了未定之二的原则。施特劳斯可能不会赞同克莱因的是,克莱因阐释柏拉图时在核心观念上大大依靠亚里士多德。 也许,依靠亚里士多德还是依靠柏拉图,造成了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差异?
施特劳斯在著述中未曾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政治哲学立场上进行某种对立,倒是常常强调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大概是为了凸显自己在古今之争中所选择的古代立场。关于这两位古代大哲之间的区别,施特劳斯的一位后学倒是有明白的说明: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强调哲人与城邦(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 碰巧,施特劳斯也这样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但是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一区别:我过去和现在都比克莱因更看重哲学与城邦(即便是最好城邦)之间的紧张。”
克莱因的著述大都在研究纯哲学或形而上学,这种搞哲学的方法和他的政治哲学立场有什么必然联系?在同一场合,施特劳斯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之后,继续说道,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相信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登峰造极的就是康德关于实践理性即道德理性的优先性教义。施特劳斯最后说:“如果我们把认为德性或道德德性至高无上的观点叫做道德主义,我怀疑,这种道德主义在古代到底是否存在过。” 难道,专攻形而上学的克莱因分享康德的道德主义?真的是这样?施特劳斯弟子伯纳德特曾断言:“克莱因把数学和道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数学与形而上学,至少在克莱因这里,是紧密相连的。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的诸德性区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与这一区分相应,又把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理智)区分为理论的(沉思的)理智与实践的(筹划的)理智,理论理智的相应对象是不变的或必然的存在,它的真理是科学性知识或智慧,实践理智的对象则是变动不居的政治与道德生活,它的真理是实践性的智慧,还有制作性的技艺。 亚里士多德认为,追问一切存在的本原与目的的哲学,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学说,哲学生活若离开一些道德德性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是,道德德性的最终根据和目的却只能在道德之外即在理论中找到,根本上,道德德性的尊严只有根据这一目的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德性本身终究不是目的,或者按施特劳斯在那一场合的说法,“如果这些德性仅仅被理解为服从于哲学且是为了哲学,这便不再是一种对德性的道德的理解” 。实践的-道德的理性低于理论的理性,施特劳斯说,这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的看法。看来,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不必然导致康德式的道德主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与城邦并非绝然对立,理论确实可以为道德-政治实践提供积极的指导,或许,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态度给了他的现代追随者们莫大勇气,使他们敢于尝试在实践理智所思想的领域寻求与理论理智所求一样的“真理”,把按照科学性知识来设计人的政治与道德生活看作哲学的“希望”。康德把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并举,这明显对应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理智与实践理智二分,但是,吊诡的是,康德在道德法则中寻求的普遍必然性,恰恰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智慧,反倒正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理智的真理的特质。康德道德主义的奥义就是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古典鸿沟,用理论来改造实践,他的哲学是现代哲人用酷似数学的纯粹哲学来筹划人的生活实践的伟大系统工程。
克莱因似乎接近康德,施特劳斯则显然亲近尼采。康德把理论与道德结合,尼采则坚定地探求在道德之外的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的秘密,因为,如施特劳斯所说,尼采深谙古典思想。现代哲人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古典派。施特劳斯不同意克莱因把道德看得过高,自称“在理论上不道德”, 同时又坚持道德对城邦生活的绝对意义,生活在城邦中的哲人对此必须充分重视,用施特劳斯的说法,逻各斯是人的本性,逻各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理性推理,一个是言语,前者对应理论生活,或者对应城邦的实践生活,两者必定“偕”一起成长。施特劳斯就是这样在政治哲学上贯彻了未定之二的原则,比较起来,克莱因毕生醉心于形而上学, 探求未定之二的本体奥秘,在这方面似乎倒不如施特劳斯做得彻底。
从古到今,哲人们似乎排成了两列,领头的一边是柏拉图,一边是亚里士多德,施特劳斯似乎跟着尼采,站到柏拉图那一列,克莱因则似乎跟着康德,站到亚里士多德那一列。克莱因与施特劳斯的区别,是不是跟他们这样站队有什么必然关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笔者生性愚钝、懒散,学和思都行之不远,很长时间也没有弄清楚这里面的必然关联,这里面也未必有什么必然关联。或许,克莱因与施特劳斯的区别问题,还可以这样来问,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什么区别,在古代与现代分别呈现为什么?
成官泯
2008年10月
导论
一
对任何一篇柏拉图对话录的解释要有任何意义,都不得不立于如下前提:
1、一篇柏拉图对话录,并非像亚里士多德的绝大多数著作或由波菲利所编辑的普罗提诺《九章集》那样,是一篇论文或讲课稿;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1447b9-11) 所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而这包括了所有柏拉图对话,甚至那些苏格拉底不是主要说话者甚或根本没出现的对话也在其中——类似于拟剧,像索弗荣(Sophron)与塞那耳科斯(Xenarchus)的作品。
2、不论一篇柏拉图对话录的目的与内容可能多么严肃,其严肃性都渗透着好玩性,既然,正如我们可以在相传是柏拉图所作的第六封信札中读到的,严肃与好玩乃是“姊妹”(323d2)。
3、不论交谈者或其他在场者可能是些什么人,我们,作为读者,也就是听众且必须一如不做声的同伴参与到讨论中;我们必须进行思量然后接受或拒绝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必须尽我们所能就存在的问题做出评论。
4、并不存在那样的柏拉图对话录,可以让我们说是体现了那也许可以并已经被称作为“柏拉图学说”的东西;一篇对话可能暗示出思想家柏拉图真正的、根本的思想,但那些思想永不会完全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关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起他自己在著述中的记录,我们有一个无可怀疑的提供更直接信息的来源;这来源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在逍遥之地,在学园呆了二十年,并且听过柏拉图本人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报道,同时绝不要忘了亚里士多德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描述其他人的思想,其使用的特定术语系统基于他自己 /2/ 的思想而非他所报导之人的思想。
5、近两百年来,学者们——不是所有但是绝大多数——试图把柏拉图的各篇对话理解成属于其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柏拉图漫长的一生中,他当然可能在很多观点甚至是最重要的观点上改变看法;但是理解一篇柏拉图对话意味着要像它所是的那样把握它,即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在其中交谈者扮演着一个特定的、惟一的角色,在其中所说的话、所发生的事并不依赖于在其他任何对话中的话与事。在我们有能力理解柏拉图思想的任何“发展”之前,我们肩负的义务是要根据其自身的意思来理解每篇对话;把一篇对话安排到柏拉图生平的某个时期对这理解并无帮助;另一方面,把一篇对话中所说的话与另一篇中的话相联系,则可能偶尔有帮助。
6、对一篇柏拉图对话录,我们必须最仔细地考察对话中说出的东西:每一句话都是有价值的;一些不经意说出的话可能比冗长的、详细的阐述更重要。
二
所有翻译者都面临如何把一篇柏拉图文本转化成现代语言、用什么话语对它解释的重大问题。麻烦是,现代西方诸语言,不论在口头语还是在“高尚”言语上,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靠拉丁语对至关重要的希腊术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术语的中转。而采纳拉丁语的这一中转,通常便造成了那些术语本来意思的一种彻底改变以及显然具有的积淀。 在拉丁语乃至希腊语的虚假外表下被歪曲的术语渗透并且污染了我们的语言。我们不停地使用着下面这些词语:actual[现实的], dynamic[动力的], potential[潜能的], matter[质料], substance[实体], theory[理论], energy[能量], logical[逻辑的], formal[形式的], abstract[抽象的], ideal[观念的], essence[本质], concept[概念], reality[实在]。我们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吗?在后面我将不使用这些词语中的任何一个,现代的“哲学”行话也将尽可能避免。/3/
柏拉图对话录的这种特性让人不可能假定有一种可称作为柏拉图“术语系统”的东西。在对话录中只有很少一些词语严格地前后一致地使用。这些词语是几乎严格地前后一致的:διαίρεσις[分析],συναγωγή[综合],和διαλεκτικὴ ἐπιστήμη[辩证的知识]。在下文中我将使用英语词“dialectic[辩证法]”和“dialectical[辩证的]”。下面这些词则带来了特别的问题:γένος,εἶδος和 ἰδέα。γένος和εἶδος常常显得是可以互换的。我们将主要而非总是用“family”[类型]和“tribe”[类别]来翻译γένος。那εἶδος和ἰδέα(它们有共同的词根 ϝιδ)怎么办呢?它们的意思很广泛,在下文中我将差不多总是用英语词“look”[型相]来翻译它们,而绝不使用拉丁语虚伪地中转的“form”[形式]或英语词“idea”[观念]以及其十七世纪的内涵。拉丁词species(来自specio,specere)本来很适合,但是,像“form”一样,英语词“species”[种类]因其积淀的意义而不能用。当柏拉图以最严格的方式意指一“intelligible[理智之物]”,即一νοητόν时,我们可以说,他的做法很“吊诡”,而这个词可以合适地翻译成“invisible look[不可见的型相]”。
三
毫无疑问,柏拉图对话录《泰阿泰德》、《智者》和《政治家》——以那样的顺序——属于一体且被设计成一个“三部曲”,不论它们是什么时候写作的。指出下面这点很主要,这三次交谈被设计成不是在三天而是两天中发生,刚好就在苏格拉底被审判及定罪之前。 接着《泰阿泰德》中的交谈,在第二天是《智者篇》和《政治家》中的交谈,而后两者之间差不多显然没有停顿。 让我们来检讨这一点。在《泰阿泰德》中,两个主要的对话者是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在《智者篇》中是爱利亚来的客人与泰阿泰德;在《政治家》中则是爱利亚的客人与少年苏格拉底,他与泰阿泰德同年,是其朋友以及运动场上的同伴。 在《政治家》中(257c7-8)的交谈一开始,客人建议应该让泰阿泰德休息一会,让少年苏格拉底来顶替他的位置。 而一会儿后(258a3-4),老年苏格拉底 /4/ 说:“昨天(χθές)我自己参加了与泰阿泰德的讨论,而现在(νῦν),我已经听到他的回答……”用“现在”一词,苏格拉底指的是在《智者篇》中发生的对话,而且客人两次提到已经在《智者篇》中考虑过的东西,似乎是,那就是一个同一次冗长交谈的一部分。 在《泰阿泰德》的结尾处,老年苏格拉底对忒奥多洛说:“明天一早,忒奥多洛啊,让我们再在这里见面。”所有这些看来都表明,在《智者篇》与《政治家》中报导的交谈发生在一段长长的时间里,从一大早持续到中午时分。我们将不得不考察这一事实,即三篇对话发生在两天里,是否有一种深意体现在交谈本身中。
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一个运动场里进行的。 昔勒尼(北非) 的忒奥多洛向老年苏格拉底引荐少年泰阿泰德,于是便开始了《泰阿泰德》中的交谈。第二天忒奥多洛则把爱利亚(意大利)来的客人介绍给苏格拉底。少年苏格拉底整个时间里一直在场, 而且可能还有很多别的年轻人也在场。 在《智者篇》开场,老年苏格拉底提了个问题,爱利亚的人们怎样看“智者”、“政治家”与“哲学家”?人们认为他们代表了一种、两种还是三种人?客人的回答是,人们把他们当作三种,他还补充道,要想清楚地确定他们每一个是什么,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在《政治家》的开场又谈到了这三者,苏格拉底则强调他们的地位非常不同。既然在《智者篇》中“智者”与“哲学家”都得到了考察,但在《政治家》中忒奥多洛和客人却表示(257a4-5与b7-c4)“智者”与“哲学家”都还有待探讨。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否在《政治家》之后得有一篇对话用来考察“哲学家”。 在《智者篇》中,客人在说到并且描述了“辩证的知识”(253d2以下)之后说(253e8-9):“现在和以后,在一些这样的地方我们将肯定会发现哲学家,如果我们寻找他”(...ἐὰν ζητῶμεν)。“如果”一词岂不是得到有力的强调吗?在《智者篇》中稍后(254b3-4),客人再一次说他们以后将拥有一个关于“哲学家”的更清晰观念,“如果我们还想要 /5/ 获得它”( ἂν ἔτι βουλομένοις ἡμῖν ᾖ )。这些话所表达的怀疑难道不是非常有力吗?在《政治家》中,老年苏格拉底说(258a4-6),他不熟识少年苏格拉底,现在(νῦν)少年苏格拉底应该回答客人,“当然,也回答我,在一会儿后。”这意味着苏格拉底设想一次与少年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家”的交谈,正如一些学者对这句话所理解的那样吗?毋宁是,这难道不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排除了这一可能性,特别是若我们考虑到苏格拉底明知道就在眼前的审判?甚至这样说也可能并不错,对苏格拉底,对哲学家的审判,取代了关于“哲学家”的对话。
四
与对话所发生的时间顺序无关,在《智者》中所处理的一些东西碰巧是《泰阿泰德》中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根源,所有事物的终极来源,“主导性的开端”(ἀρχαί),是两个东西:“同”与“异”。因此,我们将从《智者》开始,接之以《泰阿泰德》,最后看《政治家》。
对于对话中说出的东西或者没有明确说而只是暗示出的东西,我们将如何传达呢?我们将仔细阅读文本,并总是留意一直存在于其中且决定其展开方式的好玩性——严肃性的姊妹。我们将考察其说出的话语是如何造成了呈现给我们的戏剧性内容。我们将参与到讨论中:对对话文本的重述将与我们作为听众的所想交织在一起。
正如已经提到的,在三部曲中有两篇对话(即《智者》与《政治家》)都在提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智者”?什么是“哲学家”?什么是“政治家”?他们代表人之一类、二类还是三类?然而,也有其他的问题,即关于存在、虚假,以及(在《泰阿泰德》中)错误。而最主要的是这一问题:什么是存在?在这一点上引用亚里士多德也许是合适的。他说(《形而上学》VII. I. 1028b2-7):“实际上,很早以前被追寻,现在仍然被追寻,并还将总是被追寻且将总是令人困惑的正是这一点:什么是那是者?即是说,什么是存在(οὐσία)?有人说它是一,有人说他不只一,有人用一有限数来指它,其他人则用一无限数来指它。因此,对我们也是这样,那在一切之上,在一切之先,以及或可以说惟一不得不考察的 /6/ 只是这一点:什么是那被理解为存在的东西?”这些话,柏拉图在其成年的任何时间里可能会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说过。把提这一问题的柏拉图与其思想的任何[特定]发展阶段相连将会是荒谬的。
知识的问题,即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在《泰阿泰德》中一直没有回答,这并不应该让我们忽视这一事实,即知识的一些重要“片断”已在这些对话中得到揭示,[但]有时是以一种好玩的伪装方式揭示的。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点。
对话录的模仿特征所加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将文本呈现给我们的言语(即 λόγος)与行为(即 ἔργον)仔细地相互关联。在对话中说出的东西不仅是说出的,而且也是做出的,有时通过说话者,有时则通过听众,如果他们听者有意。在对话中言语与行为一直紧紧地相互联结。
对话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重复并且继续进行提问与回答。然而,不论回答可能显得多么可靠与真实,它们都必须一遍一遍地再推敲、再审查。对柏拉图,正如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活动的特征正是不节制的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