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国与现代性
-

“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
一 华夏文化的终极之词称“道”,儒道两家皆然;基督文化的终极之词称“言”,“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言是上帝。”(约一:1)然而,“道”即是“言”吗?两者可以等同,可以通约吗?若果非也,实质性的差异何在? 二 自基督之言传入华土,迄今仍常被视之为外来的异音——与民族性存在格格不入的异音。这是确实的。然而,把基督之言与西方划等号,乃一根本误识。对任何民族性存在及其文化而言,基督之言原本都是外来的异音:犹太人否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各各他的血是基督之言的明证;保罗初到雅典传讲基督之言,遭到希腊博学之士的讥讽和拒斥。 倘若使徒保罗是中国人,他会被斥为”生盲大夫”、民族的“不肖子孙”,因为,这位犹太人竟否弃自己民族的传统理念,承纳“外来的”异音。 恰当地理解这“外来的”含义:它非从西方传来——从历史现象看来似乎如此,但这全然是偶然的表象——而是从这个世界之外传来。所谓“异音”乃指,它本不是出自于这个世界,而是从世界之外,从神圣的他在发出的声音。“闻道不分先后”,同样,闻言不分先后。希腊、罗马文化最先承纳基督之言,并跟随言—说,并非等于此源初之言是它们发出的。 犹太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华夏文化一样,是民族——地域性文化,它们均有其族类的理念谱系。基督文化根本就不是民族—地域性文化。因而,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之关系不是两个民族—地域文化之关系,正如犹太、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文化之关系不是民族—地域性的关系,而是存在本体论的关系。圣言(基督)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仅在个体性的身位生成,不在总体性的民族理念。 三 希腊、罗马文化因承纳了基督之言并跟随言—说,遂逐渐呈现为一种基督文化之样式。某一民族文化可以凭其本有的语词传言基督之言,并在其文化的血肉之身中赞美或诅咒源初之言。但是,将基督文化与作为民族文化之犹大—希腊—罗马文化等同,是不恰当的,尽管晚期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以至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各民族文化确曾有,而且至今仍有一种基督文化之样式;不仅如此,将西欧的基督文化视为基督文化的唯一样式,也不恰当——例如,俄罗斯民族文化承纳基督之言后,亦形成独具特色的基督文化之样式。 任何民族性文化与基督文化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关系,不唯华夏文化独然。从历史的现象看,这种张力关系相当复杂。这不仅是说,民族存在与基督文化之间存在着承纳与拒斥的关系,也是指,民族存在既可以展示基督之言,也可能歪曲、改篡基督之言。作为例证,可以提到历史上的民族宗教对基督之言的变相,欧洲历史上以捍卫基督教为理由的民族战争、哲学思想史上希腊理念与基督之言的复杂关系,以及近代殖民主义与基督教传教事业在某些时候的互相利用。 卡尔·巴特看到,基督之身中的上帝之言乃是对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扬弃和批判,上帝之言显明了所有宗教的危机。朋霍费尔与巴特在这一点上持近似的立场。基督性与基督教并不同义同格,基督教属文化社会学范畴,指历史性的社会建制及其相关理念形态,而基智性则属生存在体性范畴,指示的是一件出自圣神的,与个体生存之在性相关的在体性事件及其相关理念。韦伯的历史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某些结果亦支持了这一见解;在历史上;所有教会组织的教义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神圣救赎价值理念(Heilswerte)的相对化形态。尼采猛烈抨击基督教——他视为历史的教会现象,对基督性却甚为崇敬。特洛尔奇从历史社会学立场否定基督教的绝对性,却并未在神学信念上否定基督性的绝对性。更为明朗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实情是:从古至今,对基督教的批判更多出自基督徒。基督徒批判基督教之根据正是基督性。 四 我因此而被要求说明何谓基督文化,如果它既非某一种民族—地域性文化,亦不可与作为一种历史性社会建制的基督教完全等而视之的话。 所谓基督文化指圣言(基督事件)在个体之偶在生存中的言语生成,这可由三项扩展性描述来说明:基督之言的历史性发生(言成肉身→对基督之言的信仰的发生(肉身与言相遇)→跟随基督之言—说(肉身成言或肉身生成位格)。 第一项描述:基督的降生——受难而死——死而复活作为基督之言(基督文化的源初词),是一个体性的发生史之事件。它不是自然历史之事件,而是圣神入世之事件。此一事件乃上帝的话语突入自然形态,使个体之偶在生存根据的根本性重设成为可能;尽管此一事件在某一特定民族和地域中具体地发生,不等于它即某一特定民族和地域性的事件。 历史文化乃是肉身之体,上帝之言成肉身,突入此地,借助了某种历史文化之体。令人惊讶的是:上帝之言成肉身选取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体(希伯来、希腊、拉丁文化之织体——新约书即为历史印证)为肉身赋灵的场所。所有的历史—民族性文化之体(无论希伯来、希腊、拉丁抑或华夏历史文化)原本地拒斥圣言,故言成肉身之史是受难而死——复活之史。尽管如此,灵与肉身的二元冲突一直存在,且从未消弥。 第二项描述:此世的信仰事件乃是一个个体性之在体论的发生事件,它关涉个体之在性的二元分离及其重新弥合之可能性。此事件之发生显现为个体的肉身偶在和处身场所之超越转换。再进一层说:肉身偶在的处身维度的二元分界不是由此世的历史和民族性之思划定的,而是圣言发生——爱的受难、牺牲和复活划定的。信仰作为个体的在性事件乃是对此二元分界的确认和跨越。就实质的文化性而言,信仰乃是此世的肉身偶在相遇那闻所未闻而闻,见所未见而见的来自另一截然异样的肉身维度的原初言词,进而不可言说而说。 第三项描述:个体偶在的肉身性在圣言赐爱的言词中向位格生成。这种生成突破此世的一切非身位性限制(历史、民族、自然地域之理念形态),向爱言的肉身之维转变。此一转变不是向上的,超出世界——肉身之外的定向,而是侧身爱言重新进入处身之维的定向。人永在此世,永无法跨越二元分界。然而,圣言已突破此一分界,成为肉身,此世之肉身生成为显爱之身位成为可能。身位之在不是肉身之在的否弃,而是对处身所在(历史性、民族性、自然性)的否弃。身位生成显为肉身之在与尽管有偶在依然发生的神圣爱言的相互寓居。位格之在的生存不是超入彼岸,而是肉身之为神圣爱言的在场空出场所。 五 由此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基督性文化与历史—民族性文化):一般所说的文化——包括各历史—民族的文化,乃是人世的自然关系和方式的培植、规范和仪式化——humanitutis cultus,每个民族都有由历史过程形成的生存方式之合理化的历史形式。基督文化乃是人与上帝(超自然)之肉身关系和方式的培植、规范和仪式化——dei cultus。前者是族群性、民族性以至历史强制性的,后者是个体性、超民族性和个体决断性的。 六 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之相遇,可以从诸方面来审视。我姑且提出四种审视角度:历史社会的、历史经典的、历史文化理念的和神学景观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否则势必造成审视规域上的混乱。 历史社会的方面,是历史—文化社会学问题,民俗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具体历史现象的基督宗教诸形态当与作为言成肉身现象的基督性在某种程度上区分开来。华夏文化及社会与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相遇和冲突,宜作历史—文化社会学层面的信仰中立的具体研究。 历史经典的方面关涉历史—文化解释学问题。每一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经典,基督临世事件的发生并以《新约全书》的经典形式确定下来,无不与人类各民族的历史经典形成张力关系,即便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张力关系,从古至今来曾完全消弥。正如韦伯所看到的,基督精神——普世性的爱不仅使所有奠立于地域性或民族性基础上的社会伦常遭到质疑,也与其历史经典形成强烈的紧张。 把旧约解释学中的预表法加以引伸和泛化,着来值得怀疑。以《新约》中的话语来解释或比附《新约》以前的经典——无论是希腊的还是华夏的;抑或用《新约》以前的历史经典来比附《新约》,都提供了一种危险,使基督性的超验品质受到损害。 各主要民族文化——希腊的、犹太的、华夏的、印度的历史经典中,都有初民摸索人神关系的话语。所有这些摸索都是人的摸索,而人的眼睛根本上对上帝是瞎的,结果是盲人摸象。上帝的自我陈述的话语与人摸索神的话语在本质上既无类比性亦无连续性。 历史文化观念方面关涉的是历史—文化哲学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经典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差异或许主要在于,基督文化之精神与历史—民族文化的观念发生了同时性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依然是多维的,例如:有与基督文化结合的希腊思想或某种犹太思想,也有拒斥基督文化的希腊思想和犹太思想。就此而言,基督文化与儒道思想的融合并非是必需的。况且,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谈论整体性的文化融合,其有效性是可疑的。 神学方面关涉个体的认信。因为,就基督神学而言,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认信——个体与上帝之关系的话语。在涉及与历史—民族文化的精神观念的相遇时,话语最终只是认信或拒信的个体表达式。以个体的身分替民族、国家、或历史文化发言,是无效的。就此而言,“中国应该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一类语式,是可疑的。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我自己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的表达式。信仰在本质上是个体与自身的斗争。 七 关于基督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相遇课题,当区分两个不同的维度:历史与发生。前者主要是历史—文化学的课题,包括历史社会的、历史经典的和历史文化观念诸方面。迄今为止,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由于大多仍在一般泛论的层面展开,尚未深入到具体个别的课题中去,因而仍然是初浅的。 所谓“发生”的维度,乃是指现时态中的个体言说(此处所谓“个体言说”,是从生存论释义学的语言理解来使用的。在此维中,谈论中国文化应该如何,难免空泛大套、一无所云。如果不是在汉语言个体言说本身的语境中直接言说基督性文化诸题旨,所谓发生的相遇就仍然还没有发生。 本色神学的论题是虚有的,因为其立论基于一个成向题的前提:基督文化等于西方文化。基督文化之中国化的论题同样如此。问题并不在于所谓基督性的中国化,而在于汉语言之个体言说领承和言说基督性,使圣爱之言成为汉语言具体的言说。 八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始处提出但未予回答的问题:“道”与“言”可以等同、通约吗?回答是否定的。“道”与“言”的首要差异:“道”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位格生成事件,“圣言”之言是“成肉身”(Person是关键!)之言。个体与“道”不存在身位间的身位相遇关系,“圣言成肉身”则是上帝作为恒在无限个体走向人之偶在有限个体,人与“圣言”的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相遇关系。相遇事件之发生,仅当两者作为个体相互走来才有可能。“上帝为何成人”因此是基督神学的基要命题之一。在儒学形而上学和道家形而上学中,“生成”理念是决定性的(易之生生;方生方成);同样,在基督神学中;“生成”理念亦是决定性的(成肉身、成人)。然,何以成、成什么,则构成决定性差异。 基督神学中的“生成”理念隐着一个本体论上的二元差异,此差异导致几乎所有神学问题的出现:恒在个体与偶在有限个体之间的本体论的断裂,并最终必然引出的“成肉身”事件之发生。儒、道之“道”理念不含有本体论的二元差异,故而“体用不二”。 此简要分疏是哲学的,而非神学的,着眼于理念之形态观审,旨在显明:基督信理与儒、道信义之融合,不仅不可能,亦无必要。儒、道理念自有其理,当自循其理路演进,基督理念同样如是。基督信理与华夏文化之相遇,从哲学观之,不是基督信理与儒、道信义的融汇,而是基督信理与汉语之肉身个体言语生成的相遇,此谓圣言之汉语生成。尽管从文化社会学观之,基督教与儒、道思想及社会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及在哲学语文学层面的分析性研究,仍然可行而且有益。至于从神学景观而论,就纯然是个体的信与不信的全然我属的自由决断之事矣。 九 近三十年来,汉语学者(大陆、台、港)对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之关系的思考和学术研究的状况,值得审理. 本文集的选编意图首先在于提供一个可供审理的文本. 文集按前述四个研究方向分类汇编:第一编为历史社会的方面;第二编为历史经典的方面;第三编为历史文化理念的方面;第四编为神学思想的方面.由于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自50年代末中断,至近年方才逐渐恢复,可供挑选的文献不多,文集主要从海外学界的文献中挑选材料,另酌量收入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 学术的积累和推进互相依赖,本文集旨在反映近三十年的学术积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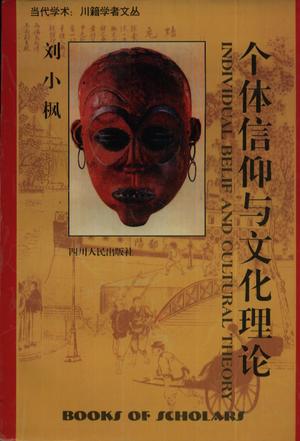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
-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内容简介:由于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一问题,我认为教会今天应采取与它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相反的行动,即应该默默地远离现在的冲突,在必要时机前保存好自己的实力,冷静地旁观,是否再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情况,是否要求它站出来说话。如果属灵危机确实发展成了1933年至1945年时的那种状况——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状况可能会从什么方向出现——那么,具体回答这一状况的要求,就会在我们中间产生,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我们应当为反对谁或支持谁作证,以及我们是否应当为这种新的紧迫情况,作好准备并如何准备,届时将会很清楚。因此,有些事将更为迫切,而不是你要我宣布的这些永恒的真理。在我看来,我们应从“巴门宣言”(Declaration of Barmen)第一款,而不是从你对“全权主义”的否定的看法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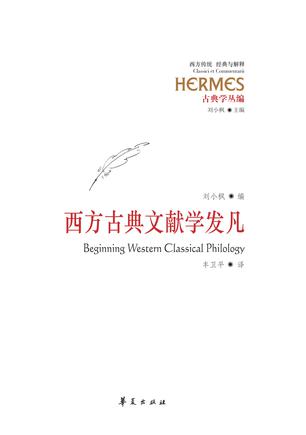
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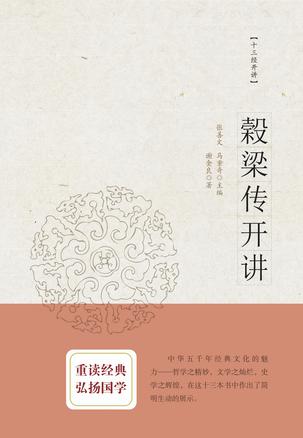
穀梁传开讲
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