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菲莉絲的情書
卡夫卡給菲莉絲的情書對深入卡夫卡的作品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他的主要作品都與菲莉絲的感情事件有顯著相關性,從《判決》到《審判》,無論是寫作時間的重疊以及主題的相關性,如果沒有菲莉絲情書的佐證,許多意義的面向都會無法被解讀而導致流失;再者,情書的型態使得卡夫卡會採取一種比一般寫作還要強烈的姿態,使他勇於將自己的優缺點與內心衝突表露出來,從而彌補了自傳的不足。 關於第一點,已經有許多卡夫卡研究者提出說明,在這裡譯者就不加贅言。 但第二點,卻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驗到的現象。 既然是情書,卡夫卡的對話對象是一位他所鍾愛的女人,從一開始的謹慎、到後來的暢所欲言、甚至分手後的關懷,卡夫卡透過情書塑造了關於自己的另一種形象,而與日記裡卡夫卡大不相同。 簡而言之,日記裡卡夫卡是自省與剖析的,情書裡的卡夫卡卻是感性與脆弱的。 情書的書寫是一種獻出自我的方式,它是一種禮物,勢必得經過包裝,這樣的包裝過程自然會有所誇張與縮減。這種修飾過自我不一定是真正的卡夫卡,卻可能是卡夫卡最在意的卡夫卡。 同樣的,情書的語言風格也迴異於一般的作品,由於它是親密對話的書寫形式,因此許多的密碼、暗語、跳躍的現象會隨著兩人感情的深入而增加。 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經常發現唯有將自己視為情書書寫者時,文句的閱讀才會通暢。 情感的配樂勢必是情書書寫的構成要素,若是缺乏這樣要素,閱讀障礙將會無所不在,因為情書不是為讀者而寫,而是為情人而寫。 這個翻譯版本的另一特色是關於書信的註評,而註評也影響到對於情書的選擇。 簡而言之,譯者不但希望透過這些情書揭露卡夫卡的感情生活、內心世界與作品的關係,更期待能將卡夫卡時代的世界圖像,以及對現代世界的意義展露出來。 因此評註並非都是直接著重文本的解讀,外在交往關係的說明、內在作品的交叉比對、相關研究的詮釋、當代世界的回應,甚至與中國、台灣文學的露水因緣,也都在評註中被提及。 作者簡介 我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於布拉格,在舊城大眾小學讀到四年級,然後進入舊城德語國立中學;十八歲開始就讀布拉格卡爾•費迪南特德國大學。 通過了最後一次國家考試後,我於一九○六年四月一日到舊環城路理復德•略維博士的律師事務所當秘書。 六月我通過了歷史性的博士學位答辯,同月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我立刻和律師先生達成協議,我只在必要時才去事務所上班,以便充分利用時間。 因為一開始我就不打算在律師這一行久留。一九○六年十月一日我開始法律實習,直到一九○七年十月一日。 佛朗茨•卡夫卡博士 譯者簡介 耿一偉 台大哲學系畢,布拉格音樂學院研究。目前從事戲劇工作,並有相關文化、戲劇與音樂評論於報刊發表。 譯有《恰佩克的秘密花園》(麥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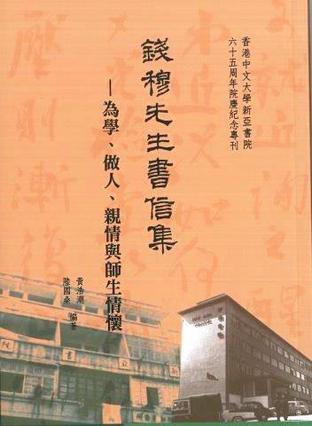
錢穆先生書信集
-

親愛的安德烈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 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 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 我要認識這個人。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MM 「你為什麼不試試看進入我的現代、我的網路、我的世界呢? 你為什麼不花點時間,好好思考「打扮」這件事,買點貴的、好的衣服來穿?你為什麼不偶爾去個你從來不會去的酒吧, 去聽聽你從來沒聽過的音樂?難道你已經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東西? 還是說,你已經定型,而更糟的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經定型得不能動彈?」 ──安德烈 36封21世紀的家書 代與代之間最好的禮物 千言萬語一扇門,等待開啟 眼看著兒子從少年變成人, 龍應台發現她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 新時代,新世界,新人類。 在封閉的兩代關係中, 青年兒女的煩惱和中年父母的挫折, 有沒有一個可以打破沉默、開始溝通的窗口? 一本跨世代、跨文化的兩代交鋒對話即將登場。你從來沒有想過,兩代人是可以這樣面對面的。藉著《親愛的安德烈》的書寫,龍應台和21歲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個透著天光的窗口。透過36封電子家書,兩代人開始──打開天窗說亮話。透過《親愛的安德烈》的天窗與天光,親愛的青年子女,或許你可以帶著這本書去敲敲爸爸媽媽的門。親愛的天下父母,也許這本書就是你晚餐桌上的讀書會,從此開始進入兒女的心靈世界。 -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玫瑰 金鎖 沉香屑 美麗蒼涼的告別 空前絕後的文學典藏 張愛玲的「信物」╳夏志清的「按語」 文學史上最難得的一場相知相惜 坦坦白白, 魚雁往返, 一筆一劃,一字一句, 張愛玲與夏志清以三十餘年的往復書簡, 告訴我們, 如何思辯、如何質疑、如何哀傷、 如何勸慰、如何任性脆弱、如何柴米油鹽…… 織造出一幅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獨特景色。 試著辨識那些字裡行間的跡證與緻密的人情紋路,然後, 我們終有一天,總算懂得人間的真實。 夏志清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從此有了精彩的開始…… 不論張愛玲的世界是華麗還是蒼涼, 張夏之間的友誼有他們的通信作見證, 他們的通信也見證了「寒□□」的人間, 畢竟還有互信的可能。 「張愛玲」,不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小說家,更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像資源。回溯上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出版《現代中國小說史》,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小姐的成就,並肯定她的位置在多數五四作家之上。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後在中國大陸,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 無庸置疑,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由這個觀點來閱讀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一九七零年代以後逐漸斷絕外界聯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與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後,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隻字都散發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夏志清先生極盡努力,把一九六三年以來所有愛玲寄給他的名片年卡和信札,憑其日期先後排出一個次序來。這些信件按時間排列,按發信的地址分成六組:一、華盛頓,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六年九月;二、俄亥俄州牛津,一九六六年十月~六七年三月;三、曼哈頓,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月; 四、麻州康橋,一九六七年六月~六九年六月;五、加州柏克萊,一九六九年七月~七二年十月;六、洛杉磯,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四年五月。通常在每封信後面夏志清會加上或短或長的按語,對信裡所載之事實及其背景做了些註解和說明,對張迷而言,將更有助於解讀張愛玲。 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於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作運動等。他更勇於發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像張當年讀夏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 -

三詩人書
在三位詩人相互通信的1926年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12月6日,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前往莫斯科停留兩個月;但是他沒有見到當時36歲的伯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 巴斯特納克已有四年沒有見到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了。自從她於1922年離開俄國之後,他倆成為彼此最為相知相惜的對話者。巴斯特納克內心將茨維塔耶娃視為更偉大的詩人,她一直都是他的第一個讀者。 34歲的茨維塔耶娃,和她的丈夫與兩個孩子住在巴黎,生活拮据。 51歲的里爾克在他最後的日子裡,身患白血病而住在瑞士的療養院。 《書信:1926年夏天》 是一幅反映藝術之神聖癲狂的肖像畫。它有三位主角:一個偶像和兩個崇拜者,這兩個崇拜者也相互崇拜(作為他們書信的讀者,他們也將是我們的偶像)。 兩位年輕的俄國詩人,相互之間有數年以工作和生活為主題的熾熱通信,他倆又與一位偉大的德語詩人建立了書信聯繫,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這位德語詩人就是詩。這三者間熱情的書信,以及他們自身,就是一個將關於詩歌及精神生活之激情無與倫比地戲劇化的範例。他們表現的是無羈的情感與純淨的熱望,那些會被我們視為「羅曼蒂克」而放棄的東西 。 德語文學和俄語文學都尤其注重精神的提升。茨維塔耶娃和巴斯特納克都懂德語,里爾克也學習過俄語,並可能通曉這門語言,他們三人都為這兩種語言所傳佈的文學神性所充溢。兩位俄國詩人自幼就是德語詩歌和德國音樂的愛好者(兩人的母親都是鋼琴家),他倆認為他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應該是某位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的語言寫作的詩人。而德語詩人里爾克則曾有一位對其影響甚大的早期戀人和精神導師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e),她出生在聖彼德堡,里爾克曾與她兩次廣遊俄國並向她學習俄文及俄國文學,他甚至因此而將俄國視為他真正的精神故鄉。 在里爾克的第二次俄國之行期間,在1900年,巴斯特納克親眼見到了年輕的里爾克,可能還經介紹認識了他。 巴斯特納克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畫家,也是很受里爾克敬重的一位熟人。未來的詩人伯里斯當時年僅10歲,里爾克和莎樂美登上火車時的情景成了他的一份神聖記憶——他們兩人契然於心、溫文、互不稱名道姓——巴斯特納克散文中獲得最高成就的自傳《安全證書》(Safe Conduct,1931)就是這樣開頭的。 當然,茨維塔耶娃沒有親眼見過里爾克。 三位詩人都因一種似乎難以協調的需求而激動:絕對的孤獨與遇見志同道合的靈魂時的強烈交心。「我的聲音只有在凜然的隱匿中才能顯得純粹而清晰。」巴斯特納克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同樣一種為不妥協精神所左右的激情,始終貫穿著茨維塔耶娃的文字。在《良心燭照下的藝術》(Art in the Light of Conscience,1932)一文中,她這樣寫道:詩人只可能有一種祈禱:不能去理解不可接受的東西。就讓我不理解好了,以便我能夠免受誘惑……就讓我聽不見好了,以便我能夠不作回答……詩人惟一的祈禱,就是祈禱變成聾子。 而在里爾克寫給許多人,從主要收信人是女性的那些信中可以看出,里爾克生活中標誌性的二步舞就是逃離、隱秘的飛翔;以及對無條件同情與理解之渴望。 儘管兩位年輕詩人宣稱他們是里爾克的追隨者,但是很快書信的往來就變成了齊頭式的交流,變成了三個親近靈魂之間的感應。那些熟悉里爾克書信之華美、通常是莊重風格的人,看到他在回覆兩位俄國崇拜者時竟然採用了幾乎和對方一樣熱切、欣悅的語調,難免會感到驚訝。他從未扮演過這樣的交談者角色。我們在他寫於1903-1908年間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中所看到的那個諄諄切切的里爾克消失無蹤,這裡只有天使般靈躍的傾談,沒有先知、沒有學徒。 通信開始於里爾克和巴斯特納克之間,仲介是巴斯特納克的父親。之後,巴斯特納克建議里爾克給茨維塔耶娃寫信,於是,通信就演變成了一段三重唱。最後加入的茨維塔耶娃卻迅速成為一股燃燒著的力量,她的需求與大膽,她袒露的激情,都如此的強烈。茨維塔耶娃是一個不輕易放棄的人,她先是懾服了巴斯特納克,隨後又懾服了里爾克。再也不知該如何面對里爾克的巴斯特納克,主動撤退(茨維塔耶娃也要求他中止與里爾克通信);茨維塔耶娃可以想像出一種愛欲的、吞噬一切的關係。她懇求里爾克同意與她見面,結果卻趕跑了他。里爾克遁入沉默。(他給她的最後一封信寫於8月19日)。 驚悉里爾克於12月底去世的消息後不久,茨維塔耶娃給里爾克寫了一封信,並決定來年為他寫一首長篇散文頌詩(,Your Death)。巴斯特納克在里爾克去世後將近五年才完成的《安全證書》,是以一封給里爾克的信為結尾的。(「如果你活著,這封信今天是要寄給你的。」) 《安全證書》帶領讀者穿越晦澀的回憶錄迷宮走向詩人情感的核心,這部作品是在里爾克的影響下寫成的,巴斯特納克或許是在下意識地與里爾克展開競爭,即便不能超越里爾克在自傳文體方面的最高成就《馬爾泰手記》(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1910),也試圖與其齊名。 早在《安全證書》中,巴斯特納克就談到過,他是為了這樣一些瞬間而活的,當「一個飽滿情感闖入,並佔據了它所面對的整個空間」。關於抒情詩的力量,從未有過如在這些書信之中如此光燦、讓人迷醉的辯護。詩不能被拋棄或拒絕,當你一旦被「七弦琴縛擄」,茨維塔耶娃在1925年7月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對巴斯特納克說的。「和詩歌在一起,親愛的朋友,就像是和愛情在一起;一刻也不會分離,直到它殺死你。」 --S.Sonta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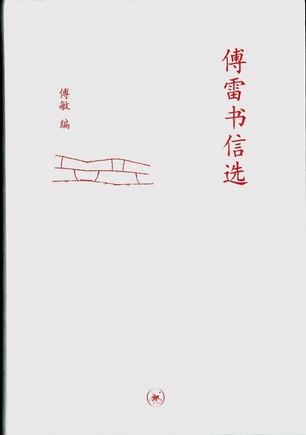
傅雷书信选
傅雷,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本书收录了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家书和亲朋好友间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