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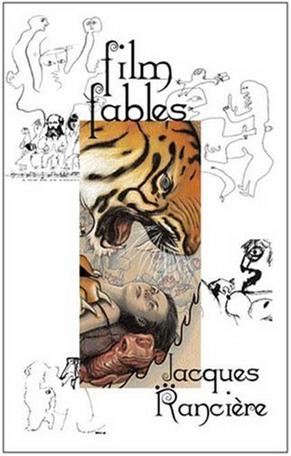
Film Fables
"Film Fables "trac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inema, moving effortlessly from Eisenstein's and Murnau's transition from theatre to film to Fritz Lang's confrontation with television, from the classical poetics of Mann's Westerns to Ray's romantic poetics of the image, from Rossellini's neo-realism to Deleuze's philosophy of the cinema and Marker's documentari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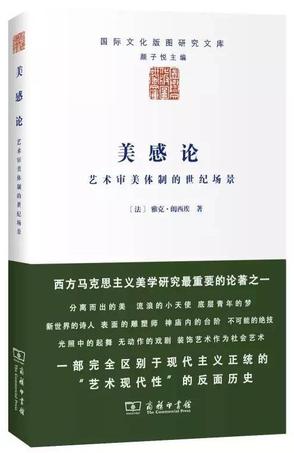
美感论
在本书中,雅克・朗西埃探讨了十四个事件或说十四个时刻,从温克尔曼笔下的赫拉克勒斯残躯,到詹姆斯・艾吉所摄的阿拉巴马州农户,间有黑格尔对美术馆的一次造访,爱默生在波士顿的一段演说,马拉美在女神游乐厅的一晚观赏,举办于巴黎或纽约的一场展出,上演于莫斯科的一幕戏剧,建在柏林的一座厂房,通过这些或闻名或隐秘的场景,我们可以探询何为艺术,以及何是艺术所为。 在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感悟、阐发艺术的体制,消除了各类艺术的专门性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间的界限,由此得以成立并转型。我们可以知道,一座缺损的雕像,如何成为一件完美的作品;一幅贫民孩子的画像,如何达成一种理想的呈现;一群杂耍艺人的翻腾,如何飞入诗意的天空;一件家具,如何被尊为一座神庙;一道台阶,如何被塑为一个人物;一件补丁累累的工装,如何像是王子的羽衣;一面轻纱的旋回,如何暗示宇宙的源起;一段加速的蒙太奇,如何表达共产主义的可感现实:这是一段艺术现代性的历史,它绝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正统。 -

歧義
政治是治理,政略則是對政治的反叛。Rancière要用政略對抗政治。 「人們一般稱政治(即police)為一種程序操作的整體,通過這些操作,組織著集體性的聚合與共識、權力的組織、位置與功能的發配,以及該發配所涉及的合法性系統。」――Jacques Rancière,《歧義》(Mésentente) 「我現在提議將la politique(即政略)保留給對立於前者(即政治)的某種明確活動,政略性活動就是將身體自它被指定的地點移開,或是改換地點的目的性的活動﹔它使得原本無立足之地得以被視見者被看到,使得原本僅佔有噪音位置者,得以論述的形式被聽見,使得原本僅能作為噪音者被聽見。」――Jacques Rancière,《歧義》(Mésentente) 《歧義》一書是Rancière最主要的一本政治哲學著作,其政治觀點繼承了阿圖塞、傅柯與德勒茲的哲學傳統。他區分了法文中的police、la politique這兩個概念,在中文裡分別以「政治」與「政略」翻譯之。Rancière認為,政治的意涵就是治理,即建立符合治理原則與利益的系統,並解決該系統在運作時會遭遇到的阻礙;相反地,政略乃是對立於政治的反叛行動,它嘗試改換,甚至破壞治理邏輯所指定的功能與系統。政略就是要求對政治進行改變,是對差異性的認同與強化,並主張保障他者的權利,這在行動上就表現為一種解放運動。 Rancière的啟迪:政治的墮落與對新政治的召喚 政治在當前社會已經從高貴的情操淪為利益的分贓,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物,Rancière企圖透過對於現實政治的抵抗,提出政略的概念,聚合多元異質的進步力量,藉此召喚新的政治形式或行動出現,他的論點對今日與未來的人類政治生活有著啟迪性的意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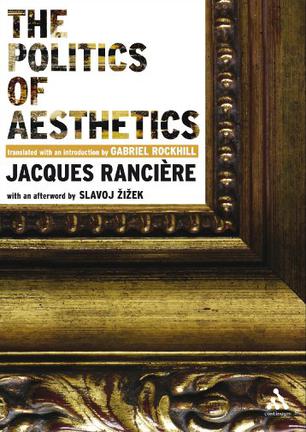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从197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著述约20本,包括他的新作《美学的政治》,其中贯穿的主线,便是压迫在以什么方式延续下来。 特鲁斯·李:“在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去世后,今天在法国政治界或知识界的政治论争,能请您大致描绘一下吗?现在法国有哪些人在用政治哲学的方法讨论问题? 雅克·朗西埃:很难说。一方面是,法国有一派正统的政治哲学,这一派的力量很强,但也很弱。有的哲学家像阿兰·芬克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米歇尔·戈谢(Michel Gauchet),他们谈民主的问题,说民主威胁到了自己,因为它正缩水成个人的、消费主义的权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拐到一种反民主的路线上,提出是因为大众的个人化,因为民主——也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什么都没有了。今天的法国很难找到有政治头脑的思想。当然还有些哲学家,比如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他争取把一种消解的政治写出诚意。 李:您以前写过十九世纪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您是不是认为,比如在法国,知识分子凭着手中的权力,在把工人归类化然后用进他们的讨论里? 朗西埃:我认为不是这样。的确,我研究了十九世纪的工人解放运动,然后来反思一个传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现在我很遗憾的说,那些话题已经引不起多少兴趣了。大家想当然,这都过去了,再没有工人运动,再没有工人解放。法国有个趋势,把各种工人抗议看成是弊端显现。工人被看成民众里跟不上时代的那部分人,适应不了现代性。 让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朗西埃用“治体秩序”这个说法,来描述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politics)的主体,即一切各居其位的社会所构造出的具体表现。治体秩序是对治理的治理或治理的过程,它规定着我们的现实或我们的感性,现实或感性涉及的潜在规则用来明确在一个具体情形中允许做什么、不许做什么,什么用的着、什么用不上,而治体秩序是在认识本身的范畴内下了规定,就像一种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一般是公司或单位里的)。因此就有一种潜在的划分,授意什么是不是能说,能见或能做。这创立了一套一套不变的规范,规范不断形成社会群体,由他们来定谁算在内谁算在外,谁的话要紧谁的话没用,谁有资格管别人谁没有。但是治体秩序里有没有实体在发挥作用?个别政治家,IT世界里的微软,或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电视公司福克斯新闻台? 朗西埃:我们不能当治体秩序不过是一种机构,我认为治体秩序跟带警棍的警察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说媒介就是治体,是种大型机器,这样说是太轻率了。治体秩序不只是那个“老大哥”,它还在安排着什么可以算进我们的经验、什么可以做。我们不一定要拿福克斯新闻台那样一个“老大哥”来说事,我认为,给我们划分可以和不可以这件事,同样也有很多有深度的电视台在做。不该把眼光只放在福克斯新闻台这种极恶劣的例子上,那些深度媒体也是治体秩序的一部分,在安排着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法国,我们有几家深度报纸,但它们像福克斯新闻台一样都是治体秩序其中一员。 李:你在找“施行政治”和“治体秩序”之间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诸众”(multitude)的书,你是不是看成一种“生于其中——自下而上”的回应? 朗西埃:以我的观点看来,奈格里的“诸众”还是在按着那个来,我会说成是用老式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政治问题,就是认为要找真正的政治舞台,一定要去生产力——活生生的力量的现实里,去社会的现实里。我认为奈格里还是着手于这样的纲领,按这个纲领所说,必有一场真正的运动来自底层,这将是劳动的运动,劳动的转型,以及新的交往形式。那还是这么一个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就是颠覆将来自系统自身,生产力为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所限,会打破旧体系。我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像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说的那样。 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美学的政治》的后记中正是强调,朗西埃描述的几种政治体系如何压制政治活动:“原政治”,是公有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和谐禁绝所有政治活动的空间。“类政治”,是除掉政治行动必需的反抗环境,用这办法来制定必须遵守的明细游戏规则。政治变形为一种“治体相关”的1——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伦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过政治”,它的核心是政治意图的悬置。这时经济基础取代了政治基础:人民政府接下来是一切事物的政府,每个人都在一个完全透明和理性的秩序内,服从集体的意志。齐泽克自己添上了去政治化的第四样系统:“超政治”,它实行中凭借直接的政治军事化,把冲突推向极端——到一个“不支持我就是反对”“非友即敌”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或以色列当局是这样来的。 从柏拉图到当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多数政治哲学家和政治体系都围绕反抗的意志这个中心,控制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按齐泽克所说,在今天的“后政治”下,可以看到政治行动中的反抗者让位给了进步的“专家政治”论者(technocrat)。治体辩护自己,不仅利用战争行动,也利用官僚姿态,和安全事务及经济上的姿态。 李:一直都有很多角色在影响公共领域。例如,布什政府一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分子”,他们就建立了一种秩序,这秩序本来可能是不合理的。这算不算一种构建世界的方式,就是说,一种“审美活动”(aesthetic activity)? 朗西埃:对,我们可以说它是种审美活动,给我们框出来什么存在,什么可见。如果你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例子:铺天盖地宣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当时,我正在美国。让我震惊的是,这不仅仅是极右的某些政客和媒体居心叵测,我记得当时很明白形势的÷拎的清民主党政客也上电视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蛊惑人心之处就在于,轻而易举就把根本没有的东西硬当成存在。用几句话就轻松办好;用不着大量的证据、讨论和说服。你就是在框出来什么存在,什么可见。当然,这个事例有些吊诡,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好是见不着的,但还是这么容易让人接受。它的核心就是这种做法,让群众经受恐怖。你有威胁了,而如果你能吓住人们,然后你就能来指派威胁他们的是什么。 李:但另一方面,您会不会把恐怖分子看成一个部分,在这其中没有参与,或是想着参与? 朗西埃:不,我完全不这么想。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做了的,算是军事和精神行动。以我的观点看来,它跟政治不沾边。搞政治是你搭台唱戏时也要让你的敌人上来,即使你的敌人不想上台,或是你还在跟他打。我认为在恐怖主义这个例子上是另一回事。恐怖主义不过是个军事问题:“你要全歼还是削减敌方兵力。”都在这了。问题是,他们不要任何人来反对压在他们头上的权力形式。 李:对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情况,谁是那些代复一代受到压迫的人? 朗西埃:巴勒斯坦人是个可悲的例子。那的情况是没有正义,昭然的非正义。同时,又很难让他们对这非正义产生一种政治意识。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是因为太多人阻碍,但他们也没做到在我们跟他们之间搭建一个政治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关于以色列的政治讨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会存在下去,不管我们怎么来看以色列建国,它的影响,还有以色列的现况。问题是,假如我是个巴勒斯坦人,以后在中东不得不跟以色列相处了,我该怎么想象这种生活?这就是我认为他们做不到的,很可悲。 在朗西埃看来,从治体秩序下解放的过程,要通过试图重新分配哪些可以察觉——哪些可说和可见,这个过程基于“普遍平等”的观念。它实际上是要让那些被当成背景噪音的声音得到真正的关切。这就像说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丢了土地的土著美国人、或吉普赛人怎么才能让人注意和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必须像说着话的人一样得到注意,而不是被看成“动物”。这会发生,只要那些没算进来的人,那些不能参与决策的人——无产阶级、妇女、非白种人、移民、流亡者——闯入治体秩序的“共识”系统,让他们自己显现出来、发出声音。在朗西埃看来,这,才是政治行动。 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过,去年法国郊区的骚乱,和今年春天因劳动力市场条例改革提案而起的抗议活动,根本上都是中产阶级输出的一种观念,要让抗议的想法保持活力,来保住他们自己的工钱。 朗西埃: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批评家嘛。我认为去年十一月郊区发生的是名副其实的暴乱,问题是,有了真正的反叛,反对某些事态,抗议某些手段剥夺了那些地方的人的上台资格,与此同时,却没有真正的政治主张。我说的政治主张,意思是人们不仅能为自己考虑,也能为别人考虑了。所以去年那更像是某部分人和国家政务之间的斗争,不过也是意义重大的。也很意义深刻的是某些知识分子精英的反应,他们说这不算什么,就是年轻的消费者们一次造反,他们最多是想要更多消费,还有说这是受了伊斯兰精神的感召,等等。这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强烈否定反抗的现实。同时,事实也是这样,反抗没有实现它这个词本来的含义和景象。 每个政治群体,也是一个审美的群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上文确立的“可感分配”,分配有什么可见、可说与可做。于是我们讨论到了审美的政治。 可感分配是政治和美学交会的地方。正是有了网络社会的互联网,博客和移动电话,还有了“快闪”族,通过临时的网络联系组织起来搞抗议——人们在预定的时间地点聚合来参与短暂而率直的集会,人们在网上传播文字,收集列表、视频和图片。还有媒体和“街头”的结合——比如对镇压抗议青年的手段不满而临时发起的游行,或是漫画一上报就有伊斯兰教徒袭击使馆,这样的行动通过让人们看见和听见来参与政治。 朗西埃给了“美学”这个概念另一个意思,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给它下的定义。他为什么没去另找一个概念? 朗西埃:说到美学,正是要重新考虑它的政治含义。在十八世纪末“美学”刚创建的时候,它跟“美”或一种艺术的哲学都没什么关系,它是经验的一个新的状态。美学意味着,第一次,给艺术作品下定义不用按它的生产规定和它送去等级制的哪一层来了,艺术作品成了一种特有的感受。这样艺术作品不再冠名给一群特定的受众或是一个社会层级。当时把这一点概念化的是康德等哲学家还有席勒等诗人,他们认为一种特有的东西,一种新平等,包含在在审美经验里。在这时候,从审美经验和审美的群体中产生一个理念,认为有可能发生另一种革命。 李:所以,您把“美学”用作一个手段,用它来理解意义是如何构成的? 朗西埃:我说的是,美学不是绕着艺术和艺术作品转的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我所说的,可感的分配。我意思是说一种方法,绘制出可见的,把可见的、可以理解的,还有所有可能的制成图。美学是经验的一种再分配,就是认为,有个范围内的经验没有进入旧有的分配,因为旧有的分配还是说人们的不同感知是按着他们在社会的位置而定,那些注定该来统治的和那些注定要被统治的本来就没有一样的感官装配,眼睛耳朵不一样,智力也不一样。美学恰恰意味着跟传统方式决裂,原来的那是把不平等具体表现在感觉世界的构建中。 李:走“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这条路可以恢复社会批评,把人们带回讨论里。它不是只观看对象,它的方法是付诸行动。这怎么联系到您的设想上,就是让沉默者上前来,来到您说的层级系统之外? 朗西埃:我认为相关美学是个在当代长起来的后代,它来自一个更宽泛的传统,属于现代性——艺术要求抑制自己,从而变成有形的生命。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想法很强烈,尤其是在苏联,画家不再在画布上作画了,但他们在成就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相关美学就是这个传统新的后裔。而且让我说,有时候它变成在恶搞那个传统了。当然,我们不该只嘲笑相关艺术,说它就是“跟人们讲画廊里没东西可以看,但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相关艺术的表现一直是很差的。 李:那些没有参与的能怎样介入进来?他们要受教育吗,该不该使用暴力?他们从哪得到授权?只要他们被听到就够了吗?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谈到“压抑之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就是发出声音了还不能得到权力、改变现状。 朗西埃:很难说需要做到什么程度。以前法国有句玩笑话,说民主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cause toujours),就是民主意思是你什么都能讲,但没有用,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看来言论自由真正的表现出来恰恰是在不该实行言论自由的场合里,它总是以违规的形式发生。政治说的也正是这个,就是你说话的那个时间和地点里本来不要你说。 以前的一次访谈里,朗西埃讲到一种“平等消灭等级或表象下的一切,也建立一个不存在正当性的社会,形成这个社会的只是字句的随机传播。一切都发生在书写的页面上。”他想象的这是互联网吗? 朗西埃:以我的观点看来,有时候互联网跟写作的本质很相似。它传播的是字句和可为任何人所用的知识。它不是要把知识给每个人,而是要让字句的传播自由和称心如意,我认为这就是互联网上发生着的。这很可能导致了某些反对分子对互联网生出这么大的气,说吓死人的是人们上了网就能找到想要的一切,说这不利于研究工作和人的智力。我说不是的,这样才成就了智力,平等的智力。你在图书馆随便走,一样也在网上这么随便逛。这就是,以我的观点看来,智力的平等的要义。 李:您说到那些没有参与进来的人,和要让他们介入。但在媒体上,有很多真人秀,像《老大哥》(Big Brother)和其它类似的节目。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是得到公共注意了,不是吗?这样是不是在把话语还给并没参与的那些人? 朗西埃:你看这有个问题,我不怎么看电视或是那些节目。我知道有人在烦了,他们说它要终结文化,终结文明,终结一切。我不看这类节目是因为我不看电视。我认为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事实如此,有了一种新的传播,一整套新的可能性。但这新的可能性流动起来就真的让更多人有了言论自由?我不这么看,因为同时也有一种标准化的民主化,一个统一标准的框架形状出所有人的体验,然后,当然,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李:说到言论自由,您怎么来看那些人,在穆罕默德卡通挑起的论战中,站出来说“我们受着压迫,西方一直在压迫我们,作弄我们的真主”? 朗西埃: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宗教信仰造成这么多的恶行,我们必须有批评它的权利。那个情况下,人们嘲弄伊斯兰教,他们是有一种特别的恨,针对穆斯林都认同那一种西方文明的解释。同时,我完全不赞同这些革命运动,我不赞同任何形式的革命,那种不允许你说这说那的。 李:您对电影有很大兴趣。最近又开始流行政治纪录片和半纪录影片,像《辛瑞那》(syriana),电影这个空间也有它政治的一面。您的这个兴趣是从何而来的? 朗西埃:电影的趣味在哪里?在某个意义上讲,在于一个矛盾的现象,电影以前遭人唾弃,算不上是真正的艺术,但现在很明显,人们想到“原创作者”和艺术的时候,他们倒不怎么想到,比如,雕刻家,而是想到戈达尔(Godard)一类人。电影现在成了,让我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的范例。另一方面,也有了这么一种可能性,给人看、给人说事情,给出一个圆的范围内的可见物景象,或我们世界的景象。近十年纪录片确实有过一阵很强的流行,想让电影参与到政治舞台上,借力于提供别处没有的信息。 李:您是不是认为,电影的发行流通很容易,这个原因让它挤掉了艺术届的位置?艺术作品、雕塑和绘画很难发行流通,相对于电影、录像和电视来说。您对电影的关注,有没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广泛影响? 朗西埃:在艺术的世界里,有强有力的讨论,也有很多形式的初步政治行动。艺术世界的一部分,介入到政治设计里,他们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做出政治行动。这个情况在电影上是不一样的。同时,电影有它的受众,不同于那些进出画廊、博物馆和双年展的人。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联系出现在院线电影和展馆电影之间,以录像的形式,电影开始流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些地方电影上映还是传统方式——电影院里你坐在银幕前——但在博物馆有多种形式来放映电影和录像,你是在那走着,停下来看一会。这样有了多种大不相同的感受。现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种双重存在。 李:作为收尾:您是个哲学家——哲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朗西埃:我不相信那个说法:哲学有它独特的身份,因此有它独特的使命。哲学没有特定的目标。这些和审美经验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我形容哲学是一个运动的空间(a place in mo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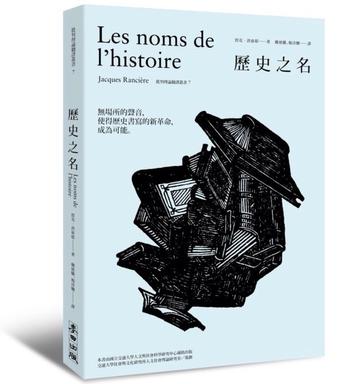
歷史之名
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洪席耶 顛覆傳統歷史思維,探討歷史敘述為知識的重要著作 ——這是一部簡短,但知識密度高,論證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與知識論批判的作品。 洪席耶論歷史之名,挑戰歷史一詞的歧義 無場所的聲音,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成為可能 《歷史之名》標示著洪席耶政治哲學的重要轉折與哲學知識新型態的成形。本書為洪席耶在康乃爾大學「寫作的政治」之講座內容。從當代馬克思主義慢慢向感性批判的理論運動移動,洪席耶透過對歷史知識進行批判的策略,將感性批判的議題顯題化,提供了這種感性批判與詩學批判的政治學談論直接呈現的可能。在本書中,洪席耶批評了自米榭雷(Jules Michelet)以來法國年鑑學派所建立的歷史論述書寫,以詩學方法檢驗各種政治修辭學的美化,以及社會科學的影響,在其中無法取得名字的歷史之間找出斷裂的空隙,破除意義與真實在書寫上的連結。 洪席耶在《歷史之名》中展現的歷史知識詩學是一種對於書寫與歷史事實之關係的哲學史筆批判,探究在語言生產活動中,語言所不能令其在場的非形式主體。如何能在這些方法之外,形成字詞與言說的過度,打開無意義的在場,不僅衝擊了塔西陀斯的修辭學式歷史書寫與其模仿的精確性,也衝擊了米榭雷與年鑑學派在弒君敘事後的科學浪漫式的歷史書寫與其社會學統計式的精確性。洪席耶提供對於historiographie的批判,提醒我們,歷史的事件性並不在於少數聰明的菁英掌握歷史可能潛在發展的規律,歷史事件透過語言的再現,有著喪失同名異義之差異而可以不斷再現的儀式性在場之風險。不在場者的在場,在當下它是以無場所的方式出現。然而這些無場所的聲音,也使得歷史書寫的新革命,成為可能。 -

沉默的言语
朗西埃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在欧美学界被誉为当代重要的美学思想家,其理论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美学与政治。《沉默的言语》是朗西埃关于美学与政治的思考在文学上的继续。他似乎想要重新描绘一个文学概念的体系,进行一种新的论证,重建一个从康德、谢林、施莱格尔到黑格尔的美学谱系。在书中,朗西埃就整个文学史范畴提出了文学的矛盾问题,在文学史中回顾文学存在的境遇问题,从比较文学角度提出了文学的多重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