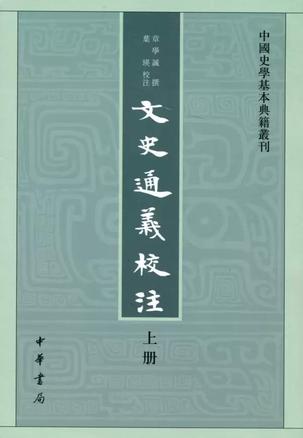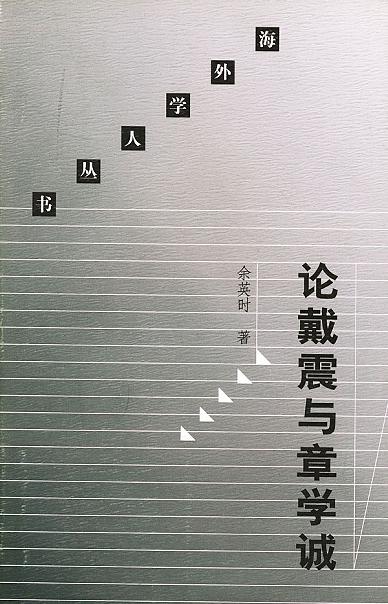章学诚的知识论
山口久和
章学诚的知识论》在"道问学"中"尊德性"
高瑞泉
2006年09月20日14:4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原是八年前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这本精湛之作现在由山口教授的高足王标博士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中国学术界,章学诚是一个并不太生疏的名字。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章学诚看作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因而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数年后则称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不过,系统的研究则当从胡适开始,那是受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刺激,两年以后出版了一本《章实斋年谱》,他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境:“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当时的胡适也只是把章看成是“专讲史学的人”,而且其研究的深度似乎尚不能与内藤湖南比肩。
从此以后,以“六经皆史”为中心来理解章学诚成为主流,或者视之为“主张‘六经皆史’的历史学家”,或者以历史主义为内核来解释其历史哲学,认为受黄宗羲的历史主义的影响,章学诚充分发挥了王阳明的命题,强调“六经皆史”: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即“六经皆器”。六经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教典籍,其中所记载的是器,说明了当其“时会”应采取的措施,这就是“当然”。学者不但应知其“当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在“器”、“史”中来认识“道”。后来龚自珍则将其发展为“诸子百家皆史”。他们的理论之核心乃在于:道展开为历史。所以只有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把握道。
另一些学者比较注意从与乾嘉学派的关系、特别是与戴震的关系来研究章学诚的思想与学术。乾嘉学派代表的清代朴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二十世纪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当初胡适就曾经将清代汉学的精神称之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进一步将之比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后来更有了余英时先生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那本书的主旨似乎是论证清代考证学的思想史意义,乃在于儒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表明了“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氏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一样是这一过程的中心人物:“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
余氏此书之作,自然有批评以研究儒学形上学为其专长的现代新儒家忽略“道问学”的意思。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的是冯友兰,但是,我们仔细一查,不仅冯友兰1934年出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没有提及章学诚。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历史哲学》等书也没有怎么论及章学诚。
概而言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汉语著述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多少显得寥落,尤其是对章学诚哲学的研究,似乎竟可以说是有些沉闷。
读完山口久和教授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随着他那如层层剥笋、如蚕茧抽丝一样绵密的论证,在那些已经近乎老生常谈的话头后面,一个新的章学诚豁然呈现。
毋庸赘言,山口教授对于有关章学诚研究的各种文献,包括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透彻的了解,因而在自己与章学诚的文本以及上述二手研究三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对话。作为一个曾在京都大学接受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课程训练的日本学者,他对资料的占有之详实、考辩之精审,相信可以经得住最挑剔的审视。不过,作者的宗旨并不在于对章学诚思想进行历史的客观的整理和分析,而在于对章学诚的哲学做创造性的诠释。换言之,用我们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通常见到的长于实证研究、短于理论创造来看待山口教授的这一著作,是完全的错置。借用章学诚的范畴,毋宁说,这部著述的特点是:在沉潜功力中透出高明性灵。
中国读者将不难发现,与通常集中在以“六经皆史”来把握章学诚的著作不同,山口教授的这本书“试图在实斋复杂多样的主张背后解读出对知识主观契机的恢复,从中对他的思想进行整体把握”。这里有一个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
日本的中国研究对历史分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中国近代(宋、元、明、清)的成立,具有平民的发展和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参照《东洋文化史研究》所收《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两个根本特征以自由研究、自由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形式的细分化出现了,传统的“学问”发生了知识和智能的分离。在其末期,因为种种因缘,知识的主体即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从“儒者”(Confucian)向“学者”(Scholar)的转变。所谓“学者”,山口教授“将它作为一个有别于生活感情、信仰伦理、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智识活动从事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使用。大概比较接近西欧的humanist这个词汇所持的含义。”从事此类多少有些价值中立意味的知识活动、或者说是中性的知识活动,本身成为一种职业。于是出现了类似后来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描述的那样:“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这样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及其生存方式,在阎若璩、章学诚等“学者”身上,有了最初的体现。这与德川时代(1600——1876)的日本发生的情况有某些相似,甚至很可能是近代化来临前的普世化现象。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判据上面,才有所谓“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因为韦伯式的学术“知识”,它表现出一种自律倾向,即以知识自身为目的,故而有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同时,知识生产也表现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趋势,它的进步同时还由于既有的知识在时间流中存在着被修正和超越的可能性。——这使它区别于神圣性的知或经学家所追求的永恒的“道”。那么,这样的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动力何在?在这样的追问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端倪:知识以自身为目的,目的因转变为动力因,“学者”的存在或学术活动的主体性自身即是动因。借用章学诚的范畴,就是在“尊德性”的导引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
山口教授在细密的行文中不断揭示,通过对占据主流地位的考据学的批判,章学诚如何在“道问学”的土壤之中滋养“尊德性”的精神。山口教授说:“向‘尊德性’的倾斜,在‘专家’(此处的‘专家’是指章学诚所说的能‘成一家之言’的人——引者注)那里是头等重要的。余英时借用柯灵乌的用语,把知识所拥有的这种契机称为‘先验的想象’,我则想强调它更接近德国解释学派的‘前见’(Vorurteil)——学术活动中的预先判断——这个概念。”章学诚高度推崇的“神解精识”、“别识心裁”,其最初的动因正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微妙的契合:“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缁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是否“切己”,才是引起主体关注的关键。
对于人们说的章学诚“发现有我”和“发见自我”,山口教授以为这就是“主观性的自觉”。与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中主体性概念——纯粹理性的认识主体——不同,这里的“自我”、“主观”应该在解释学的框架中展开。它不再只是干燥的理性之光,而指向了完整的人,因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具体概念,不仅包含了认识活动中的“前见”,而且有所谓“性情”,更进而达到“人格”。章学诚尝曰:“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即使是考证学这样貌视客观的学术活动,其真正的动力,也只来源于天生的资质和真诚的感动。而它们最终指向着“性灵”。如果在康德认识论中,“我”作为统觉,是知识经验的首要条件的话,“性灵”是文史之学中的“我”,它使知识经验统合化;这种知识活动本身又反过来培养着人的性灵。换言之,章学诚的认识活动从“我”出发,又指向着“我”。也许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山口教授断言:“可以说实斋的‘性灵’观念是最能表现其全面推出认识主体主观性的特异学术论的概念。”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诠释章学诚之清代考据学批判而展开的。这一批判,从“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的不同意识,进而扩展到一般的方法论和语言哲学领域。与实证主义的考据学强调归纳与演绎的逻辑不同,章学诚重视对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直觉;与考据学强调从局部推向全体的认识路径不同,章学诚以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对“宗旨”的把握,它比对细部的认识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这种方法论上的分歧,与对传统的言意之辩的不同解答有密切的关联。以追求圣人之意为中心的考据学,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就是经学的文本可以表达神圣的知识;而将“性灵”置于知识活动中心的章学诚却更倾向于“言不尽意”的传统,“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
不难发现,章学诚对清代考证学的批判,正可以映照出山口教授对当今日本中国学主流的质疑。此书掌握资料之周详、对相关论点的考辩之精审,在我读过的中国哲学家专论中,实在是罕见的。这表明作者是真有资格采取如下的态度:本书自序中,作者毫不讳言他对拘守实证方法这种保守性的批评。而其内里,是来自对所谓“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解释学方法的自信。狄尔泰曾经说,在精神科学中,精神的联系,作为一种本源上给定的联系,是理解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我们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进入他人的内心,进入人文世界。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拿着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作为工具,生硬地肢解中国古代文献,或者像蜘蛛吐丝般演绎出似乎大有新意的老生常谈。《章学诚的认识论》与它们全然不同,统篇给你的感觉,就是著者与章学诚之间那种深刻的“精神的联系”,通过理解章学诚,著者也敞开了自己的性灵。这在学术越来越被现代学院体制所“规范”,人文学科的研究和著述活动越来越服从商品交换法则的今天,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山口教授在将此书稿交出版社的同时,嘱我为其做序。章学诚自己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文史通义·匡谬》)我对章学诚并无专门研究,本非作序文的合适人选。只是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与我的怂恿推荐有关,所以自觉有向读者推荐之责。但是,写下这些文字,决不敢说我已经明了“作书之旨”,而只能借这篇急就的读后感来表达我内心的羡慕之情:尽管我像本书作者一样希望看到读者、特别是章学诚研究的专家们的批评——在此一定存有开放的空间。但是我确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成为章学诚研究的新界碑,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