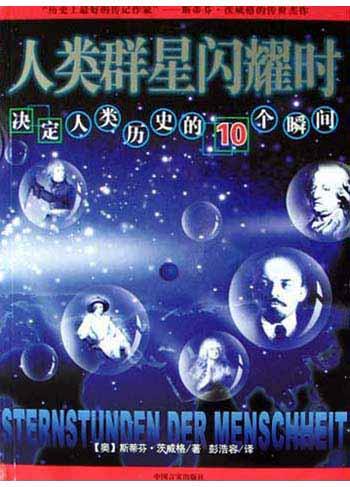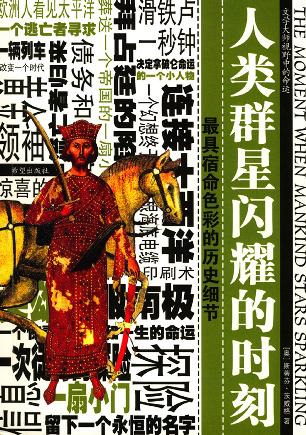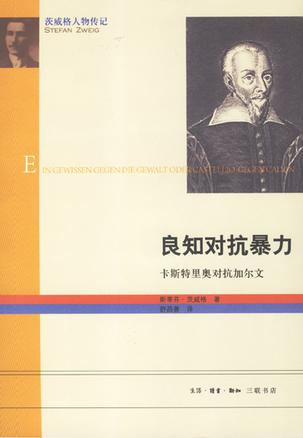与魔鬼作斗争
斯蒂芬·茨威格
简介 《与魔鬼作斗争》论述了三位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生活历程,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精神导师倾向,在生活中总是从精神上苛求自己,追求人类精神自由、完美的巅峰状态。
本文选自其中论述尼采的篇章《没有其他人物的悲剧》。
没有其他人物的悲剧
获得存在之最大享受意味着:危险地生活。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脚戏:在他的一生这短暂的场景里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在雪崩一样坍塌下来的每一幕里,这个孤独的战斗者都独自站在自己的命运那雷雨交加的天空下,没有人站在他身旁,没有人走近他,没有一个女性以温柔的存在来缓和那种紧张的气氛。所有的运动都仅仅由他发出也仅仅跌落回他:为数甚少的几个开始时出现在他的影子里的人物只是以无声的吃惊或恐慌的姿势陪伴他的英雄冒险,渐渐地像面对什么危险人物一样退却了。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近或完全踏入这个命运圈子,尼采总是独自诉说,独自战斗,独自忍受痛苦。他不对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回答他。更可怕的是:没人听他的。
尼采的这出惟一的英雄主义悲剧没有人,没有搭档,也没有听众:但它也没有真正的舞台,没有风景,没有舞台布景,没有戏服,它好似在思想的真空领域上演。巴塞尔、南堡、尼斯、索伦特、西尔斯—马利亚、热那亚,这些地名并不是他真正的家,而只是他以燃烧的翅膀飞越的道路两旁空洞的里程碑,是冷冷的背景,无语的水彩。实际上这出悲剧的舞台布景一直只有一个:独自一人、孤独、那种让人恐惧的既无言也无回应的孤独,这种孤独像他的思想背负着的、在他的周围和头顶的一座无法穿透的玻璃钟,一种没有鲜花、色彩、声音、动物和人的孤独,一种甚至没有上帝的孤独,一种所有时间之前或之后的太初世界里的冷漠死寂的孤独。但是,使他的荒凉、孤寂如此可怕、如此恐怖而又如此荒诞可笑的是一种不可思议,那就是,这种冰川和荒漠一样的孤独在精神上竟然发生在一个美国化了的、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铁路隆隆电报嗒嗒、熙攘嘈杂的新德国,在一种平时总有一种病态好奇心的文化里,这种文化每年向世界抛出四万本图书,每天在上百所大学里寻觅问题,在上百所剧院上演悲剧,但却对这出发生在他们自己中间,发生在他们内部圈子里的最宏大的戏剧—无所闻,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因为正是在其悲剧最伟大的时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德语世界不再拥有观众、听众和证人了。起初,当他还是一个讲台上的教授,当瓦格纳的光芒还使他清晰醒目时,当他最初开始谈论时,他的话还能引起些微的注意。但当他越是深入剖析自己,深入剖析时代,他就越少引起反应。当他进行英雄的独白时,他的朋友们和陌生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他们被他那些越来越狂野的背景变换,被这个孤独者越来越狂热的激昂吓坏了,他们把他独自一人可怕地留在了自己命运的舞台上。渐渐地这个悲剧演员变得越来越不安,这样完全对着空无讲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喊叫,越来越手足并用,只为能引起一丝反响,或者至少引起一些异议。他给自己的话创造了一种音乐,一种奔流汹涌、狄奥尼索斯的音乐——但没有人再听他的。他强迫自己演一出滑稽戏,强迫自己尖利地、刺耳地、硬生生地开怀大笑,他让自己的句子疯狂地跳跃。他插科打诨,只为了能用艺术性的愉悦来为自己可怕的严肃吸引听众——但没有人鼓掌喝彩。最后他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在刀光剑影中的舞蹈,他伤痕累累、流着血在人们面前表演这种新的致命艺术,但没有人能够领会这种叫闹的玩笑的意义和这种硬装出来的轻松背后那种身负重伤的激情。没有观众,没有反响,这出被赋予我们这个衰落的世纪的前所未有的精神戏剧就这样面对着空荡荡的长椅结束了。没有人哪怕稍加留意,这只在坚强的顶端飞速旋转的思想陀螺怎样最后一次庄严地跃起,最后蹒跚地跌向地面:“死于永恒之前。”
这种“与自己同在”、这种“面对自己一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活悲剧的最深层意义和惟一神圣的苦难:从来没有思想如此巨大的丰富、感情如此膨胀的疯狂面对世界如此巨大的空无,面对这种金属般难以穿透的沉默。他从来没福气得到一个出色的对手,所以这股强劲的思想意志只得“向自身挖掘”,只得借“挖掘自身”从自己的胸膛和自己的悲剧性灵魂中获取回应和异议。不是从世界中,而是在血淋淋的撕裂中这个命运狂人像赫拉克勒斯撕下内萨斯衬衫一样从自己的皮肤上撕下那种燃烧的热情,只为能够赤裸着站在最终真理面前,站在自己面前。但是包围这种赤裸的是怎样一种寒冷、围绕这种精神的高声呐喊的是怎样一种沉默、覆盖这个“谋杀上帝的人”的是怎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的可怕的天空,现在,由于没有对手发现了他,他也再难找到对手,他只好向自己进攻,“毫不留情地做认识自我的人、做自己的刽子手吧!”被自己的魔鬼驱逐出自己的时代和世界,甚至驱逐出了自己的本质的最边界,
被不知名的狂热震动,
在锐利冰冷的寒箭前颤抖,
我被你追逐,啊思想
你这不可名状的、蒙面的可怕思想!他有时以极度惊恐的目光回望时会不寒而栗,因为他发现他的生活已经把他抛离所有生存着的和曾经生存的东西那么远了。但这样一种超强力的起跑已经无法再回头:他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下,同时又在自我陶醉的极度兴奋中去履行那种由他热爱的荷尔德林为他预示的恩培多克勒的命运。
英雄的风景中没有天空,宏大的演出没有观众,沉默,越来越强大的沉默包围着精神孤独的可怕呐喊——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要不是他自己极度陶醉地对此说“是”,且为它的惟一性而选择并热爱这惟一的残酷,那我们一定会把这场悲剧当做大自然众多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之一来憎恶。因为他凭着最深刻的悲剧直觉自愿地、清醒地从安全的生活中建立起这种“特殊的生活”,并且单凭勇气的力量向众神发出挑战,要在自己身上“试验人类在其中还能生活的危险性的最大强度”。“你们好,魔鬼”尼采和他的语言学朋友们在一个大学生式的欢乐的夜晚用这样一句亵渎神灵的欢呼宣告了自己的力量:在鬼怪出没的午夜时分他们把满杯的红葡萄酒洒向窗外巴塞尔城熟睡了的街道,作为向那些看不见的幽灵的祭礼。那只是一个用深刻的感觉来推动自己的游戏的绝妙的玩笑:但魔鬼们听到了这声欢呼并跟上了这个邀请它们的人,直到这个一夜之间的游戏变成了一场命运的壮丽悲剧。但尼采从来没有阻止过这种可怕的要求,这种要求有力地抓住了他并且带着他飞驰:锤子越是有力地凿在他身上,他意志的坚硬石块就越发出愉快的声音。在痛苦这块烧得通红的铁砧上,随着每一次双重的敲打,那用以给他的精神包上一层坚硬的盔甲的公式被锻造得越来越结实,这是“人类之伟大的公式,对命运的爱;即人类不想要别样,不想向前,不想后退,不想躲入任何永恒之中。对必然的东西不仅仅是承受,更不是隐瞒,而是热爱”。他对力量这种热情的爱的歌唱声以奔放的气势压过了自己痛苦的喊声:瘫倒在地上,被世界的沉默压碎,被自己撕碎,被所有痛苦辛酸浸蚀,他却从没有举起过双手,命运最后只好放弃了他。只是他还祈求更多的东西,更强烈的苦难,更深刻的孤独,更完全的痛苦,祈求自己能力的极大丰富;他不是在抗拒中,而是在祈求中,在英雄一般的庄严祈求中举起了双手:“被我唤作命运的我心灵的天意啊,你在我之中在我之上请保护我,留给我—个伟大的命运吧!”
谁知道如此伟大地去祈求,谁就会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