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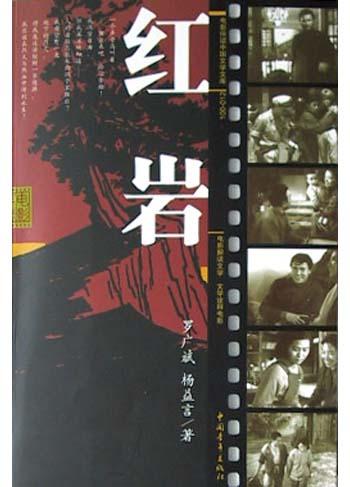
红岩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罗广斌(1924-1967),四川成都人。中学时即参加革命活动。1948年被捕,先后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解放后任职于共青团重庆市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曾编辑重庆集中营死难者诗集《囚歌》,与杨益言、刘德彬合著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并出版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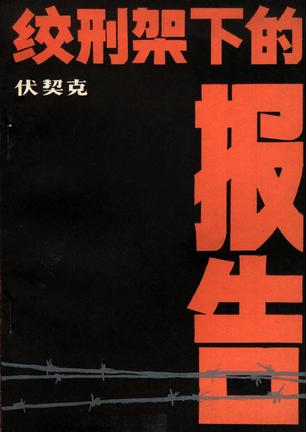
绞刑架下的报告
作品的手稿共167页,稿纸规格不一,文字篇幅各异,它们是在沦陷时期由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们秘密带出来的。此次出版的《报告》首次完全按照作者的一张张便条式的手稿原样进行排版,恢复或补充了在以往版本中被删改的文字或段落。新更正或补充的部分均用黑体字来标明。
《报告》第十版以前的版本中均缺手稿的第91页,直到后来才找到了这一页。
此次出版的策划者们有意保留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所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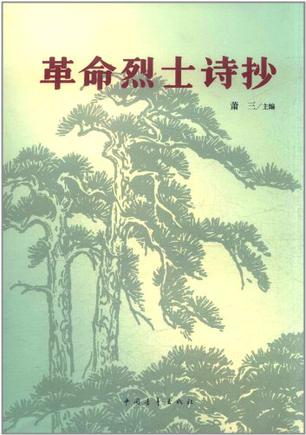
革命烈士诗抄
《革命烈士诗抄》内容简介:这些烈士们的珍贵遗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满腔赤忱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表现了革命先烈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和愿为革命粉身碎骨的坚强决心,同时也体现了革命先辈对前途乐观、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正是这些革命先烈——新中国的创造者、奠基人——为了我们今天的事业,在我们的前头光荣地牺牲了。作为后死者的我们,则更任重道远。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战斗成果,并且应该加以发扬光大,是他们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亿万人民群众造就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则要把她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光荣义务。 我们学习这种诗与人的“革命回忆录”,对于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建立革命人生观与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大有益处的。 -

狱中书简
《狱中书简》是一本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的集结。这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感,还是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海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 作者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便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心灵的另一面。这《狱中书简》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读着这些信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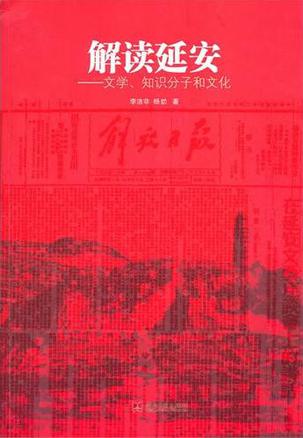
解读延安
《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内容简述的是延安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延安时代对20世纪中国文化,其重要性都超乎想象。“延安”就像一粒纽扣——系上它,20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便“旧貌换新颜”;同样,只有解开它,才能看见历史和文化的内部发生了什么。 -

革命与情爱
“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逐渐走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而引发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政治与性别认同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界等问题。“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是对动荡和剧变社会的文学反映,最早呈现在1920年代末。在对这个流行却比较不受人重视的文学公式的研究中,本书作者所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主题重述是变化着的文化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而这一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 《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将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写作公式“革命加恋爱”作为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喜爱,直到1970年代还影响着主流的中国文学。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革命话语的变化是如何促成了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难以预料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革命加恋爱”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 ,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刘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特征;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王德威 一部扎实、迷人的专著……将会引发个体能动性、女性身体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历史的讨论。 ——美国《中国研究》(China Journa) 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1991)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还没作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是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