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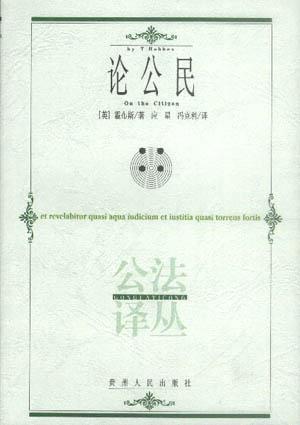
论公民
致读者的前言 我向读者承诺,包含在此书中的,皆是人们通常认为有助于凝神阅读的东西:重要而有益的题目、研究它的正确方法、出色的说理、写作的诚意以及作者的良知。在这篇前言中,我会对这一切作个简短的说明。此书要阐明人的各种义务——首先是作为人、其次是作为公民(citizen)、最后是作为基督徒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了自然法和各国法律的原理,构成了正义的源头和力量,构成了基督教的实质(在我的计划所允许的限度之内)。 远古时代的智者相信,将这类教诲(与基督教有关的除外)传给子孙后代,只应当采用优雅诗文或朦胧寓言的方式,以免人们所说的统治(government)那高深而圣洁的神秘性,被私人的议论所玷污。同时哲学家也很活跃,有些人在观察事物的运动和形态,这于人大有益处;有些人在沉思事物的性质和起因,这于人无害。后来,据说是苏格拉底最早爱上了这门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那时它还没有被理解成一个整体,只是——不妨说——在公民统治(civil government)的迷雾中初现端倪。据说,苏格拉底极为看重这门科学,他摒弃了哲学的所有其他内容,断定只有这一部分与他的智慧相称。继他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其他哲学家,最后还有各民族的所有哲学家,甚至不仅是哲学家,还有那些闲暇时光中的绅士,都想在此一试身手;这种努力不绝如缕,好像它是无须努力就可轻易入门的学问,它向一切天生有此爱好的人敞开大门任其取舍。赋予这门科学以高贵性的最大因素在于,那些自认为掌握这门科学或处在应当掌握它的地位上的人,即使只知其皮毛也洋洋自得,所以,他们乐于让其他学科的行家被人视为聪明的博学之士,或被人这样称呼,却绝不希望他们被人称为通晓治术者[Prudcnt0]。由于这种政治专长非同寻常,因此他们认为只应当把这个称呼留给自己。判断一门学科之高贵性,不论是根据掌握它的人之尊贵,还是根据著书立说者的数量,或是根据最聪明者的判断,这门学科在他们中间都肯定享有无与伦比的高贵性。它属于君主,属于以统治人类为己任的人。几乎人人都会乐于拥有它,哪怕只是一知半解;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倾全力加以探究。如果我们想一想,有关这门学问的那些错误的夸夸其谈,会给人类造成什么伤害,那么假如正确地传授它,即它是从正确的原则中得出的自明的推理,我们对它的益处即可一清二楚。当我们作为智力训练思考某个题目时,若有谬误悄然溜入,除了时间上的损失,这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在人人为了生存方式而应予思考的问题上,谬误甚或无知肯定会导致侵犯、争执和杀戮。正因为这种伤害是如此严重,恰当阐明义务的教诲才显得如此有益。有多少君主本身是好人,却因臣民可以合法弑杀暴君的谬论而丧命?基于某些理由,有人可以剥夺至高无上的君主对国家的主权,这种谬论让多少人死于非命? 又有多少人因为君主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其妈仆这个廖见遇害?最后,这样的教诲——君主这命是否符合正义完全由私人决定,在君主之命得到执行以前,人们可以正当地对它进行讨论,而且事实上也应当议论——又引发了多少叛乱?当前的道德哲学中还有许多危险性不亚于此的观点。在此不必一一列举。我认为古人对此是有预见的,因此他们宁肯把正义的知识隐匿于寓言之中,而不愿付诸公众的讨论。 …… -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
丹尼尔·贝尔较为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在理论专著越来越难读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今,贝尔的这种方式,算得上是一种反拨,至少是跟古代的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接了轨。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气势汹汹的术语,只是通过一条一条的设问,归类,推演和反驳,就把问题引向了自己所需要表达和阐述的中心里来。事实上,贝尔在这本书的开始篇章“为对话体一辩”里,首先就是提到《理想国》这个先例,并且认为“英美政治理论中正在进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似乎特别适合使用对话形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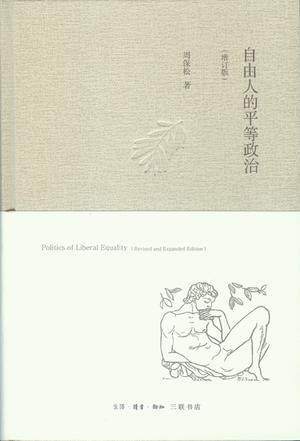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增订版)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作者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作者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

原罪与正义
此书系六点学术丛书。作者刘宗坤为北大哲学博士和美国Valpraiso University法学博士。此稿部分内容曾在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系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并经过作者技术性的改动。 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认同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下,它随着西方文化对神圣性的遗忘而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因此,重新梳理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是当今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关键一环。 首先,《原罪与正义》从哲学背景和它在宗教文献中意义的演进与继承等几个方面,展开阐述。其次,基于上述概念的梳理,《原罪与正义》进一步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中“罪”观念是如何通过自然法理论,并在历史上宗教因素的作用下,而影响到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理论之于近代政治思想的意义在于,它为建立所谓“有限政府”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此书对西方文化中的罪论作出理论上的概念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西方文化中的罪论和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社会政治维度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联系。内容丰富扎实,注疏详尽,叙述精准,思考深入,这些工作,增强了国内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深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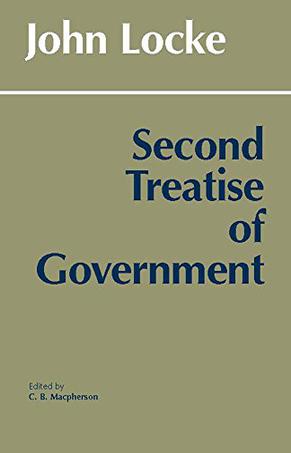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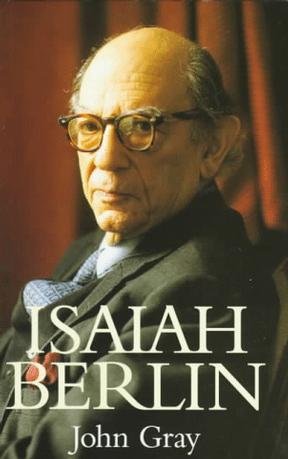
伯林
如果说写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个令人胆怯的任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在伯 林著作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异常清晰的。虽然伯林的著 作涵括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许多作者,但它们并非各自分离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题;与 之相反,伯林的各种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所有伯林的著 作都是由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着并使之获得生命力的。我把这个观念叫做价 值多元论,其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 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 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本书的大部分篇 幅将用于阐释和评价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 都被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 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和恶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理性弃我们于危 难而不顾、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我把伯林的由 价值多元论引致的这种政治观称为“竞争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 “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它有两重含义,既是指对唱比赛中的竞争或竞赛也是指悲剧 中人物的冲突。与我们时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即乐观地认为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当 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谐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和悲 剧的自由主义,它认为在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价值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任何选择 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不像历史上的和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那 样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谐共存的,也不赞同辉格党的历史哲学(这些自由主义就 是与这种历史哲学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为自由理性传统提供了 富有希望的生机。如我将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他的价值多元论以及他 所坚持的人性的历史主义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类的一般性观点之间的无法消除的矛 盾,情况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他一方面受惠于维科和赫 尔德,另一方面又与J.S.穆勒的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而导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种历 史主义观点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基于理 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就可以消解这个矛 盾。我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根据,伯林或许也不同意这种办 法。根据对伯林思想所作的这种维科式的和赫尔德式的解释,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 的竞争而是竞争的多元论。 伯林思想的深刻独创性和颠覆性有助于解释那些异常的事实——直到目前为止,对 这种异常的事实仍缺乏专著式的研究。确实,在伯林的理论活动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会 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这种独创性和颠覆性。在本书中我必须做很大的省略,尽管这些省 略都有一些可辩护的理由,但由于遗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终究总是一种遗憾。 我没有利用亨利·哈德拥有的伯林关于许多论题的未出版的文献,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 出版的资料。对于伯林关于认识论问题和意义理论的早期哲学论文,除了指出它们都反 对实证主义把一切有意义的论述都归结为一种模式的主张,也许这预示了伯林后来对一 元论价值论的攻击,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东西。除了间接地或附带地涉及到一点外,对伯 林在俄国研究中所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他在战争期间作为政治观察员所写的一些报告 (这些材料有些曾在《华盛顿通讯》发表),他对音乐的爱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没有予 以论述。我也没有提到他的许多表现友谊的事例,这些必须等到由米歇尔·依格纳铁夫 (Michael Ignatfeff)撰写的伯林传出版后才能为世人所知。对于伯林的个性与他的 谈话(这些谈话在表现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绝的)和思想(他坚信,还有 许多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着的现实、正当、价值等) 之间的联系,我也没有做出说明。我只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和体 现这些思想的哲学概念方面,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义的理论成就 和他确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现在我只就与他的思想有关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 俄国的里加(Riga),像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样,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 德(Chabad Hasidim)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 在里加长大,讲俄语和德语。他家1915年从里加搬到安得里普(Andreapol),1917年 又搬到彼得格勒,在这里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然 后在拉脱维亚停留了短暂时期后于1921年到了英国。他的祖父、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和 三个表兄弟于1941年在里加被纳粹杀害。他在圣保罗学校上完中学,在牛津基督圣体学 院受的大学教育。除了有三年时间他先住在纽约后又到华盛顿为英国政府工作,以及 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时间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这里,他一直作为全灵学 院的研究员,1957—1967年担任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会主席,1966—1975年担任沃尔夫 森学院的院长,1974-1978年担任英国研究院院长。此后,他在牛津度过了他的大部分 时间,谈话、写作和出版作品。 人们经常把伯林与休谟作对比。这种比较一般并不会形成什么误导,但却遗漏了许 多重要的东西。像休谟一样,伯林后来也放弃了哲学而转向对历史的研究,虽然休谟研 究的是英国历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们都是运用其哲学观点于历史研究的典范。 如果伯林与休谟分享着一种深刻的理智上的快乐,一种对思考和写作中表现的清晰透彻 的风格的热爱以及一种对历史的讽刺的爱好,那么伯林自己还有一些为和蔼可亲的休谟 所缺乏的偏好。这种偏好来源于伯林的多元性的继承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英国人的而是 俄国人和犹太人的,这就是他对观念和人类生活中悲剧感的偏好。伯林曾经说过(实际 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 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 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 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 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 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 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 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 的传统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满活力的人类生活概念,——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 把它称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实最令人感动的解释”——是一种悲剧性的概 念,这也是一种与任何神义论的观念所抵牾的观念。我认为,伯林这种悲剧思想的根源 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犹太人遗传。正是这些分离的多元性文化遗传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 思想中形成多种观念的微妙缠绕,这些只有借助于扎实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