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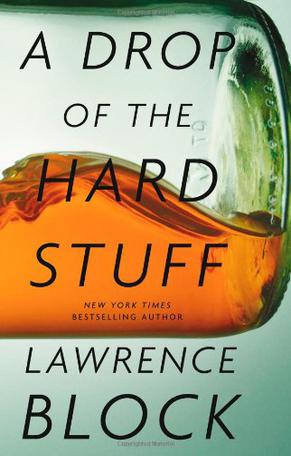
A Drop of the Hard Stuff
Matthew Scudder is finally on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when he runs into "High-Low" Jack Ellery, a childhood friend from the Bronx. In Scudder, Jack sees the moral man he might have become. In Jack, Scudder sees the hard-won sobriety he hopes to achieve. Then Ellery, following to the letter the dictates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infamous twelve steps, is shot down while attempting to atone for past sins, and Scudder is drawn into a murder investigation that threatens to upset his path toward recovery--and get him killed in the process. Exploring themes of loss, nostalgia, and redemption, for Lawrence Block, A DROP OF THE HARD STUFF circles back to how it all began, reestablishing why the Matthew Scudder series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innacles of American detective fiction. -

譚納的兩隻老虎
伊凡‧麥可‧譚納現年三十四歲,自從在韓戰期間遭到一個砲彈碎片擊中,破壞了睡眠中樞以來,他就沒有闔過眼睡覺。譚納喜歡追求無望的理想和女人。聯邦調查局裡有他的厚厚檔案;中情局則竊聽他的電話;一個超級機密的情報局希望吸收他成為他們的密探。他擁有各項才能和特殊的人脈,這使他成為極機密危險任務的不二人選──而這類任務如果出錯,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譚納總是會碰上新鮮事,好在他有許多時間去一一加以探索。這次他只不過想讓他的小女孩米娜玩得開心。米娜是立陶宛遜位皇室的唯一後裔,但她仍然只是個小女孩──她很興奮能去參觀蒙特婁的世界博覽會。但皇家加拿大騎警隊、一群魁北克恐怖份子和不知名的美國政府機構都各懷鬼胎……一場單純的出遊卻讓他和米娜陷入一場恐怖計畫中,而這不只是個一般的恐怖計畫,它是史上最大膽、最卑怯的計畫……就是將英國女王炸成碎片! -

八百萬種死法
美國當代冷硬首席大師卜洛克代表作「馬修‧史卡德探索」系列,已堂皇進入正統文學的殿堂。 這可能是閱讀情境最接近台灣現狀的一部推理名著:紐約有八百萬人,有八百萬個故事,有八百萬個死法… -

騙子的遊戲
「我們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未來。」 他不是成為一名冷血殺手,就是一具冰冷屍體! 一名行騙度日的男子,一只藏有海洛因的旅行箱,一場拿性命作為籌碼的騙局…… 喬.馬林是個年輕的騙子,仗著那看起來強壯又富有的軀體──結實的肌肉,下斜的雙肩,窄窄的腰身,曬成古銅色的肌膚──從好騙的女人身上拐錢度日。 他剛離開一個錯誤的對象──他看走眼了,一副有錢人模樣、有著漂亮胸部的琳達.詹姆森,其實是個想釣金龜婿的窮酸女孩。他離開費城,下一個落腳處是大西洋城,然後,他在海灘上邂逅了穿著連身紅色泳裝、溼漉的金髮還在滴水、紅潤的雙唇看起來充滿饑渴的蒙娜.布若薩德。 他的人生從此起了劇烈的變化。 不只因為蒙娜,還包括藏在他偷來的旅行箱裡,一大盒高純度海洛因。 喬.馬林想擁有蒙娜,以及不虞匱乏的幸福人生。現在他得執行他生涯中最危險的騙局、一場拿性命作賭注的遊戲,他的下場不是成為一名冷血殺手,就是一具冰冷屍體…… 喬.馬林,這是我的名字;是我還沒叫大衛.蓋維蘭,也還沒叫蘭尼.K.布雷克或其他一大堆名字之前的真名。 姓名重要嗎?從來就不重要。 但出於某些該死的理由,我希望她喊我喬…… -

衣櫃裡的賊
鎖——羅登拔世界的必要之惡 名記號學者兼小說家的安博托.艾可在他《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中曾這麼講過,「生命,是從有了界限開始。」 我不確知這麼一句智慧延展力十足的哲語,是否在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生物學、物理學等等每一門學科中都禁得住考驗捶打,但讓我想到生物學家的一種說法。 我想,這個說法多少有著隱喻的意味——他們講的是生物細胞最外層的「薄膜」,細胞膜,這個狀似脆弱無比、乍看之下好像只勉強區分了生命內外界限的薄薄一層,生物學家以為卻是生命形成極重要、極睿智的一步,因為它「必須」是個半透明層,意思是某些物質可以穿透,某些則被排拒在外,這是生命成立的兩難,因為生命必須攝食,讓可供維生的新陳代謝物質進來;但生命又同時得想法子遠離侵害,讓那些不受歡迎的東西不得其門而入。 然而,從攝食面來看,生命的新陳代謝卻又意味著你得想法子突破攝食對象的防衛機制,悍然侵入它這層半透明的薄膜——這是生命本質深處難以言喻的最終殘酷性。 有沒有可能獨沽一味把這層膜無限強韌化到任何侵害都進不來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首先,生命本身便遭到徹底的封閉隔絕,沒有任何生存所需的東西可以到手,也就是說生命告終,死了。 似乎生命的成長和危險根本來說是共生的。 如此,讓我想到了桃花源,幾年前,大陸那邊據說終於找到了陶淵明筆下那個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和平美好世界,我私心底下一直希望這消息是假的,或至少只是好事倖進之徒的驚人之語而已——當時,名小說家鍾阿城人正好在台灣,談起此事,阿城磕著不離手的煙斗,只悲憫的說,「慘啊!」 阿城說,所謂的桃花源多得是,戰亂起了,苛捐雜稅來了,年成不好了,盜賊群聚了,總會帶出一批「避秦」之人,如果找到一個以當時歷史條件而言完全與世隔絕之地,比方說陝北哪個山坳裡或某個孤島,短期來說,這就是桃花源了,但你頂好求天保祐別就這樣長期隔絕下去,否則不用幾代下來,你便會看到一個退化到意思接近死亡的聚落 ——阿城說,所謂的退化不只是和大歷史發展脫節、生活形態徒留從前的問題,這還有幾分文學哲學的境界,更麻煩是幾代近親通婚再加上知識的停頓,所必然呈現人的白痴化問題,阿城說他在大陸便看過不止一處這種所在。 也許,生命真的從有了界限開始的,但得是一種半透明的、可進出的界限。 羅登拔工作簡介 我們說過,柏尼.羅登拔不是亞森羅蘋,他是我們這一代的賊——在現實世界的秘密不斷被揭露,很多動人的想像失去了現實的依據,遊俠的廣大冒險國度消失殆盡,仍奮力在壅塞冷漠的城市中保有最原初「賊的夢想」的一個好賊。 他幾乎是可信的,而他在實踐上也像個孜孜勤勤的工作者,不像亞森羅蘋那樣像個無所不能的神,或至少像個可以不具實體的幽靈。 亞森羅蘋會宛如末世先知般,先君子的預告下手的對象,某日某時某刻他會大駕光臨取走某物,然後在法國警察佈成的天羅地網中忽然瀟灑現身,得手揚長而去——這正是古龍小說《楚留香》的出處,「當踏月來取。」 然而,羅登拔的工作程序卻大致是這樣子的:他得先探知哪家哪戶值得一偷的對象,某時某刻離城渡假或外出看戲,並先到該處進行必要的偵察,等工作的時刻到來,他會換上他的 Puma 鞋、帶著紐約警察視為他標誌的剪去手掌部分的外科醫生用薄手套(既要保持雙手靈活又要避免留下指紋),拎著他裝有開鎖工具的手提箱出發。 他得小心在遠離對象幾個 block 之處下計程車,然後想法子通過或警戒或打混的大廈管理員(有關此點,羅登拔有很多精妙絕倫的好用招式),坐電梯但不直撲目標所在的樓層,再循防火梯步行下樓(或上樓)。 在正式開鎖之前,他得小心先撳門鈴,最後確認一次是否屋內有人,然後他會興味盎然告訴我們門鎖的數量、品牌、其弱點及其強度,這才表演般拿出他的偷竊工具,以最輕柔但最快速的手法喀喳打開來。 你記得偉大神奇的亞森羅蘋實際上開過幾個鎖嗎?還是他只像魔術師般只唸唸芝麻開門之類的咒語,人間所有的鎖自然會聞風解體呢? 羅登拔最違背闖空門守則的是,他進入一間空屋子到實際下手取物之間,總會忍不住耗時欣賞屋內的品味和佈置,想像屋內家居生活的溫暖模樣,他甚至會拿本書坐上舒適的躺椅翻個兩頁——羅登拔是個愛書的人,在這個系列中,他白天的正當職業是一家二手書店的獨資老闆。 通常,羅登拔先察看的很奇怪是冰箱(他也很奇怪為什麼很多女屋主總認為這是藏現金的最安全地點,我個人因此回家敬告老婆,該換個收現金的地點了)。他以為做個好賊得擁有鑑賞力,你才知道該拿走什麼留下什麼,包括珠寶、稀有錢幣、郵票、棒球卡或甚至有特別紀念價值的書籍版本等等,然而,羅登拔最喜歡的仍是現鈔,一種無記名的、不用轉換銷贓的最高流通性通貨,」好神奇,當你把別人的現金放入自己錢包裡,它立刻就變成你的了。」 亞森羅蘋,我個人印象裡是不偷現金的,他會認為這太粗俗了——因為書中的亞森羅蘋永不缺錢,甚至不食不飲。 其他的珠寶、錢幣、郵票等等都不會「立刻變成你的」,因為它們得送到可靠的銷贓者手上,需要耐心等它們被兌換成現金,而羅登拔是知道行情的,他所能落下的,了不起只是真正價格的三成左右而已。 膽小,勤奮,熬夜工作且執勤時間絕不飲酒,專業知識和技藝,風險不低,回收讓亞森羅蘋嗤之以鼻(儘管羅登拔自己總是十分滿意),而且警察隨時找得到你人在哪裡,這樣一個現實的賊,但羅登拔仍樂此不疲,仍講述起來讓我們如夢如幻如一則不敢想像還存在的成人童話。 一則鎖與鑰匙的簡易歷史 然後,我們來談一下鎖的問題——賊的世界之中一種「必要的惡」。 我們的柏尼.羅登拔先生常自言(事實上是大言不慚的自詡)是個天生的賊,他自舉的天賦異稟理由總不外乎這麼兩點:一是精神狀態方面的,指的是他每一次順利破門而入,面對著一個空無一人的屋子(或公寓房間)那一剎那,一定會同時湧上來的難以言喻緊張、激動、甜美和混雜著自傲的滿意之感,千金不換;另一則純粹是身體方面的,也就是他一再自詡自己對開鎖的異常天份和「觸感」,他說這門技藝當然需要不斷的練習精進,但前題是你得先有天份,就像一切關乎創造性的行業和學問一樣,比方說寫好的小說或發見物理學的動人原理。 讓我們從這樣一個不算太聰明的問題問起:究竟有沒有一種理想的鎖,是沒有任何了不起的賊——當然包括了羅登拔先生在內——可以打得開的? 當然有的,而且既不是什麼理想的鎖,甚至根本也談不上進步二字,據可信的歷史考證加推斷,人類所發明的第一個鎖就是打不開的——也就是說,鎖的漫長歷史是從不能打開開始的。 今天我們所知道最早的鎖可上溯到古埃及時期,有四千年之久,但不是實體,只是壁畫上所繪的形象,真正的第一個鎖出土自尼尼微郊區的廢墟——從形態來看,便是這樣一種打不開(或正確來說,從外頭打不開)的鎖,樣子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大體上是一根橫木穿過兩個直立木頭中央的孔洞,呈雙十圖樣,就像很多人鄉下外婆家老房子木門至今仍在使用的、或尋常寺廟大門仍保有的、我們稱之為門栓的東西,這個古老的鎖,外頭沒有鎖孔,當然也就沒有鑰匙,也就是說,在鎖的發展史上,我們今日視為連體嬰的鎖和鑰匙這兩個部分,其實是分別出生的,而且誕生的時日還相隔好一截。 據了解,鑰匙誕生於稍後的古希臘時期。 這種無法自外頭打開的鎖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不方便,你得非保持有人在家不可,而且這樣的鎖除了使用在門戶之外,無法進一步拿來保護你隨時要放進取出的東西,如我們今天常用的旅行箱或保險櫃等等,換句話說,這種不存在鑰匙的鎖,從外部來看,是純封閉性的,管你是誰,一概立入禁止,不選擇,也不辨識。 從這個角度來看,鑰匙的登場便不只是鎖的補充或附件,而是根本上改變了意義和使用幅度——它開啟了鎖原來那種不分青紅皂白、拒人千里之外的徹底封閉性,讓鎖成為具選擇性的半透明層,符合它辨識的歡迎進來,不符合的謝謝光臨;鎖也因此變得無所不在,舉凡人們所珍視的、要保護的,都可以鄭重的加個鎖於其上。 然而,主人進得來,盜賊於是乎也跟著進得來,世事總是這麼回事不是嗎? 從鑰匙出現這一刻開始,理論上,宇宙間再不可能存在任一副完美的鎖是賊永不可能打開的了(你也看過諸如○○七情報員裡那種用瞳孔或指紋辨識的鎖,結果核子彈還不是照樣被野心的恐怖分子盜走)。這個全新階段的遊戲變成:兩造各自發展,彼此見招拆招,就像生物史上肉食動物和草食動物的演化追逐競賽遊戲一般,也像中國那則「我刺穿你,或你擋住我」的古老矛與盾寓言。 凡財貨處皆有鎖 而且,鎖的進化還存在著一個根源性的弱點,很難克服,那就是它正常時候得方便被(主人)打開,因此它不能肆無忌憚的儘往複雜困難的方向走——這羅登拔也認真告訴過我們不止一回,比方說像輔助性的防盜警鈴一類的東西,當然很難克服,你得在開門自然啟動它的十秒內找到它並予以關閉,但更多時候是屋主裝置之後廢棄不用,理由是屋主自己不會每次返家入門都記得執行這個必要動作,往往出現和老婆或女友衣服脫了一半、警方持槍破門而入要你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的尷尬場面;或很單純只是覺得麻煩而已。 這是賊的小小優勢。 這裡,讓我們稍稍折回頭一點,想一下為什麼會有鎖的出現。 鎖是一種保護裝置,保護我們認為有價值而且我們擔心會遭人搶奪竊取的物件——光有價值但不擔心會遭搶奪竊取之物不在此限,比方說陽光、空氣和大部分時候的水,有價值得不得了,但我們並不去鎖它們(儘管人類繼續這樣為非作歹下去,可能也快得考慮這麼做了)。 擔心遭人搶奪竊取的根源在於稀少性,而正如每一部經濟學教科書一開卷就告訴我們的,資源的稀少性是經濟學思維的前題,也當然就是私有財產制發生的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說,鎖的歷史意義,正是私有財產制的一個醒目的標誌,它必然稍稍晚出於私有財產制的出現——從反向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歷史上滿多人這樣的)把私有財產制視之為惡,視為人性自私、貪婪的墮落,鎖的守護神意義也就成為幫凶,是更好世界出現時一定要打倒取消掉的東西。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們中國歷代老祖宗對所謂大同盛世最簡單、最具說明性的招牌講法,不正正就是向著鎖來嗎? 人的自私貪婪且不容他人染指之物,當然很快就不限於自然界已有的有形之物而已,鎖也就呈現了從用法到形態的多樣性:我們把食物金屬珠玉視為財貨,鎖起來;把女性的身體和所謂貞潔視為財貨,也鎖起來(貞操帶的構造便是一種以鎖為核心的怪物);把統治的權力、面子、言論和意識形態視為財貨,也鎖起來(這種人形的新鎖一般是去了腦袋的肉食性有生怪物,稱之為錦衣衛、東廠太監、蓋世太保、耶穌會、KGB、CIA、警備總部……等族繁不及備載);把國家視為財貨,也鎖起來(軍隊、關稅、萬里長城、通電鐵絲網的高牆……)——甚至在言情的羅曼史世界也有類似的需要和應用,畢竟情感也是稀有、獨占、不容他人鼾睡染指之物,我們稱之為「心鎖」或「情鎖」。 如此遍地是鎖,你會不會開始感覺到年少時唸過的一些社會主義回頭來覓你,夢啼妝淚紅闌干的又浮上心頭呢? 當這個社會哪天再沒有錢了 好吧,既然都提到社會主義,我們就順勢再多社會主義兩下吧——其實談賊的話題扯一點社會主義是自然而且堪稱宜當的,因為賊既然是負責開鎖的,是對付私有財產守護神的,是搖撼這罪惡私有財產制度的,賊於是有著某種英雄式的光環,比方說,溫文儒雅的英籍社會主義史家霍布斯邦便寫了一部名為《盜匪》的專書,書中,我們清楚可以讀到,在學術良知和行規的可容忍範疇之下,霍布斯邦已竭盡所能為盜賊這個行業辯護了。 羅登拔所說對現鈔這種瞬間產權轉移的驚喜,其實不僅僅是俏皮話而已,且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及些微的職業性憂慮埋在其中。 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發展到今天,貨幣的重要性一再被確認(貨幣老早就不再是沉默透明的交換工具了),但同時貨幣的形態和意義也不斷的複雜起來(可參閱名經濟學家傅利曼的著作)——這裡,我們只就貨幣使用最浮泛、最日常生活的現象面來看,當交易和財產記錄及其移轉的透明度愈來愈高,交易使用現鈔的範疇和額度愈來愈小,粗魯來說,也就是每個人所需要和願意保有的現金愈來愈少,一個賊還能偷些什麼?或者說,這個古老可敬的行業會不會凋零消失呢? 我個人會說,羅登拔這樣的賊會,但賊不會。 賊當然不會,只是偷法不同,怎麼個不同法呢?比方說,直接當駭客侵入某個機構的電腦系統直接在記錄上動手腳或盜出信用卡密碼;或比方更古老的,花錢選上個立法委員或縣市首長,來個五鬼搬運等等,也就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那一套——很抱歉,這方面的神通及其奧祕,我個人所知道的太有限,只能做提示性的說明。 冷酷的偷,粗魯的偷,明目張膽的偷,毫無優美技藝、鑑賞力和信念的偷,就只是少了羅登拔這樣優雅、浪漫、瀟灑且充滿人性的賊——在賊的發展史上,也一樣存在劣賊逐良賊的可悲定律。 我們可能誰也改變不了這樣一路下滑的拋物線走向,但我們可以讀羅登拔,記得一個這樣的好賊,並做為他日 raining day 時用來烤暖雙手和胸口的柴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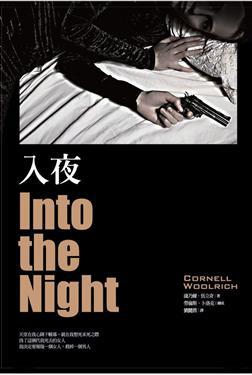
入夜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一聲槍響,兩名女子的生命路徑,自此交纏糾葛 一份遺稿,兩位推理大師,跨時空接力成就一段絕妙曲折的懸疑故事 困在絕望深淵的寂寞美女瑪德蓮考慮自殺。她輕輕撫摸一把醜惡的左輪槍,那是酒鬼父親唯一留給她的遺物。她用槍管抵住太陽穴,扣下了扳機,只聽到清脆的撞針敲在空彈膛的聲音。 自殺失敗讓瑪德蓮如釋重負,欣喜若狂,重拾了對外來的希望。她隨手把槍一拋──子彈卻以無比憤怒的速度擊發出去,不偏不倚的打中屋外路過的年輕無辜女子。她死在瑪德蓮的臂彎裡。 這是《入夜》的開場,濃縮康乃爾.伍立奇寫作精髓的壓卷之作,塵封已久,未曾面世。伍立奇苦思多年,始終無法完成這本愛恨交織、懸疑激情的小說,在他死後,遺留下這部推理小說史上最深的遺憾。而這本凝聚大師心血的小說,由勞倫斯.卜洛克──現今最具風格的推理小說作家,續成出版,足可與伍立奇其他經典──《後窗》、《魅影女士》、《黑衣新娘》並列,絕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