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兰经故事
《古兰经故事》是以《古兰经》讲述的故事传说为基础加工编写的融知识性和文艺性为一体的通俗读物,在选材上力求忠实于《古兰经》原文。故事内容的详略取舍,力求与《古兰经》及其经注相吻合,某些细节描写和气氛渲染,力求有所依据和参考。《古兰经故事》的重点是古代众先知的故事,人物按其所处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为了保持内在联系较密的多则故事之间的连贯性,《古兰经故事》把它们合并为一则,如“以色列三代君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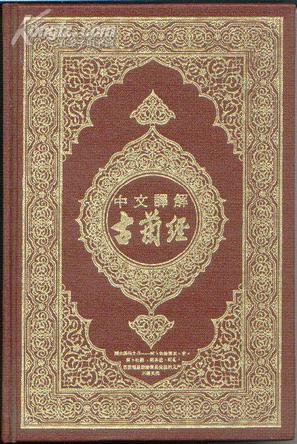
中文译解古兰经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وترجمة معانيه إلى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中文译解古兰经 مجمع الملك فهد لطباعة المصحف الشريف 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局 译者简介: 马坚先生(1906-1978),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回族,中国云南省个旧市沙甸村人。早年曾就读于云南省昆明明德中学,后到西北宁夏固原,师从著名经师虎嵩山学习伊斯兰典籍。 1929年到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商埠和港口城市上海,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专修阿拉伯语及经籍,兼学英语,1931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同年12月由中国回教学会选派,随中国首批留埃学生团赴开罗,1934年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预科,1939年毕业于开罗阿拉伯语高等师范学院。1939年至1946年期间辗转于上海、云南等地,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并潜心于《古兰经》的研究和翻译。1946年到北京大学工作,一直担任东方语言学系教授、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49年曾作为中国穆斯林杰出人物,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从1954年到逝世前,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坚先生还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后任该会常务委员,此外,还曾担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等职。 马坚先生通晓汉、阿两种语言文化,兼通波、英两种语言,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从事伊斯兰学术研究和阿拉伯语教学科研工作,其卓著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马坚先生曾翻译出版过大量宗教著作,其中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是《古兰经》全译本。马坚先生毕生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他的宿愿,传播伊斯兰教义,直接作用首先是帮助中国穆斯林克服语言障碍,领悟古兰真意,消除教派隔阂。早在1934年他在开罗发表《中国伊斯兰教概观》一书时,就曾对中国穆斯林中某些偏离教义的现象和教派纷争导致“老死不相往来”乃至“近乎引起流血冲突”的问题作过具体的分析。此后他又在1949年出版的《古兰经》汉译本(上册)译者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古兰经》,也就不能本着《古兰经》的教训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发扬文化,为人民服务。”因此,他把翻译《古兰经》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对好友纳忠先生表示,翻译《古兰经》是他一生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表达了让天下穆斯林都能在古兰精神的照耀下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根本大愿。1939年,他从埃及学成归国后,潜心《古兰经》翻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经文前八卷译注本(即前面提到的上册)。但在此后的20年间,因忙于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发展以及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整个译稿的修改和加注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 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正如中国当代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马坚先生译的《古兰经》于1981年在中国出版后,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此后,又于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随《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

阿里与妮诺
全球28种译文,中译本首度推出!皈依穆斯林的神秘犹太作家,文明冲突、宗教歧异下的爱情裴歌,欧美大学比较文学必读书。里海之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高加索山下的《日瓦戈医生》。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讲述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饱含热情、诗意、幽默与悲怆的骤然转换,读起来却又感到具有史诗的幅度和辉煌。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短暂而多事的岁月,地点在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自称卡特维尔),以及波斯(1935年以后称为伊朗)。阿里·汗·席尔万希尔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中学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爱上了十分美丽的妮诺·吉皮安尼,这是一位格鲁吉亚贵族姑娘,基督徒,信仰格鲁吉亚东正教,受到欧洲式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具有欧洲人的思想方式和感情倾向。为了相亲相爱,这一对男女青年克服血仇报复和众人的非议,走过因为开采石油而热闹又杂乱的巴库街道,穿过空旷而优美的沙漠,在遥远的偏僻山村逗留,然后来到阿里·汗叔叔在邻近的波斯首都德黑兰的豪华宅第。最后,这对情人又被吸引回到巴库。但是,战争和爱国主义影响了他们的前途,阿里·汗必须做出决定,是保持对于自己亚洲人先祖和祖国的忠诚,还是为了对妮诺的深厚爱情而置其他于不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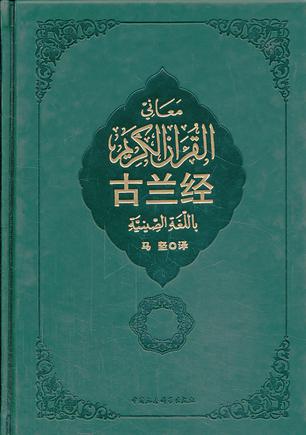
古兰经
古兰经据称是安拉在穆圣二十三年(公元610—632)的传教活动中适时地零星地用阿拉伯文降示的一部综合性大法典。一千三百年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各国穆斯林信仰和遵循的一部根本法典。它既是伊斯兰信条的源泉和教法创制的依据,也是一切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和道德规范的准则。古兰经有多种中文译本。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马坚先生的译本随《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我社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马坚先生的汉译本,一直畅销不衰,并远布海外,在国内外穆斯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被沙特阿拉伯定为国际汉文《古兰经》钦定本。此次应广大读者要求,新版重印,以全新的面貌面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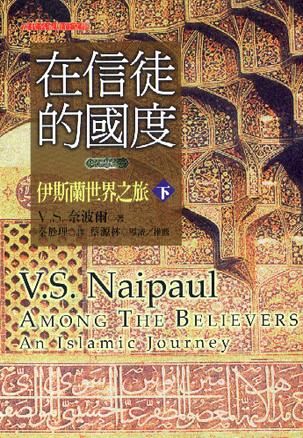
在信徒的国度(下)
一九七九年年中,V. S. 奈波爾取道亞洲大陸,輾轉七個月行旅,並以這段旅程為基礎,探索四個伊斯蘭國家的常民生活與文化,以及四國內部波瀾起伏的政治激流:伊朗,革命的怒火與歇斯底里持續延燒﹔巴基斯坦,自從標榜為印度裔穆斯林建立祖國,獨立建國以降,三十二年來,還是宿命性的一籌莫展,萎頓於未開發狀態﹔馬來西亞,政局由穆斯林獨攬,經濟卻由構成全國百分之五十的華人寡占﹔印尼,無解於穆斯林身分與文化根源之衝突,困惑於不到四十年間,四朝執政(其中兩番遭到外來政權把持)之興替與殺戮。奈波爾描繪了一個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教世界,其間唯一動力來源,只有堅此信念、窮且益堅、深信不移的信仰意志。 -

走向圣城
伯顿爵士根据自己在东方圣地上的亲身经历,对东方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他不仅详实地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异国风景,各种或宏伟壮观、或令人惊叹、或朴素无华、或令人感慨的清真寺建筑,清楚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四大主要派别,向读者展示了他眼中的伊斯兰教各种仪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考察,对东方人、对东方风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前言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 de 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 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人们。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 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 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并选择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神自新过程。 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 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资料是值得阅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书。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 《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驻波斯的大使。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子。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惋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 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 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 《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 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 周 宁 2007年12月 代译序 第一部 埃及 第一章 走向亚历山大城 第二章 离开亚历山大城 第三章 尼罗河汽轮——“小哮喘号” 第四章 客栈生活 第五章 斋月 第六章 清真寺 第七章 准备离开开罗 第八章 从开罗到苏伊士 第九章 苏伊士 第十章 朝觐船 第十一章 去延布 第十二章 逗留延布 第十三章 从延布到阿巴斯泉 第十四章 从阿巴斯泉到麦地那 第二部 麦地那 第十五章 从麦地那郊区到哈米德的家 第十六章 拜谒先知清真寺 第十七章 先知清真寺历史篇 第十八章 麦地那 第十九章 库巴清真寺 第二十章 拜谒哈姆扎之墓 第二十一章 麦地那人 第二十二章 拜谒圣徒之墓 第二十三章 大马士革旅行队 第二十四章 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 第二十五章 希贾兹的贝都因人 第二十六章 从苏韦尔吉亚到麦加 第三部 麦加 第二十七章 首次拜谒禁寺 第二十八章 首日礼仪 第二十九章 次日礼仪 第三十章 第三日礼仪 第三十一章 令人憔悴的三天 第三十二章 麦加生活和小朝 第三十三章 麦加的朝拜圣地 第三十四章 吉达之行 译后记 伊斯兰圣地与西方人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