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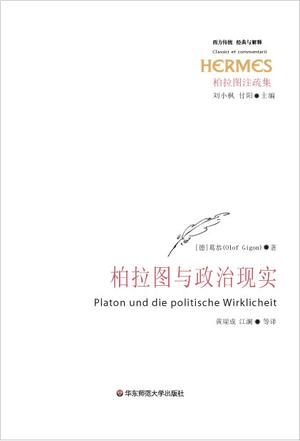
柏拉图与政治现实
《柏拉图与政治现实》收集了古典语文学家葛恭的四篇重要的柏拉图研究论文,对柏拉图的若干对话(如《法义》、《普罗塔戈拉》和《游绪弗伦》等)做了精彩的疏解。作者展现了一位德语古典学家深厚的文献学功力,每篇文章都非泛泛之谈,其分析触觉之精细、文献视野之广博,的确令人大开眼界。《柏拉图与政治现实》表明,关注和细究柏拉图作品的文学(修辞)性乃西方古典学界的传统之一,并非施特劳斯的首创——毋宁说,即便关注柏拉图作品的文学性,仍然还有一个视野问题。《柏拉图与政治现实》还表明,西方的古典研究要从维拉莫维茨一耶格尔的历史主义古典学传统中走出来,何等艰难,尽管葛恭已经难能可贵地摆脱了当时在德语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对古典学的不良影响。《柏拉图与政治现实》的出版,为汉语读者提供了如何贴身细读柏拉图对话文本的精彩范例,对汉语学界重建自身经典的家法统绪有着特别的启发。 -

设计论证
卢梭在西方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地位显赫,无需多说,他出于何种意图以及如何改变了文明人类的一些基本假设,却需要我国学界花费大力去探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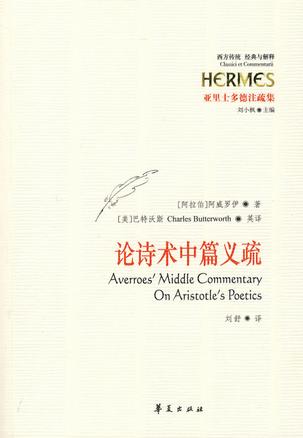
论诗术中篇义疏
阿威罗伊似乎不满足于阿拉伯文化中众所周知的诗的原则,这促使他作一篇中篇义疏来解释亚氏这篇著作。在注疏过程中,他表现出一种引导阿拉伯诗本身转向的愿望,希望它抛弃琐碎、不负责、甚至纵欲、放荡的关注点,转而服务于道德目的。正是因为人们能从诗人富于想象力的表达中获得愉悦,能从朗诵押韵的整齐诗行中享受快乐,诗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说服工具;诵读诗句最初是因其悦人的形象或者动听的声音,现在除这个功用外,还可以用它来形成意见和思维模式。 ——巴特沃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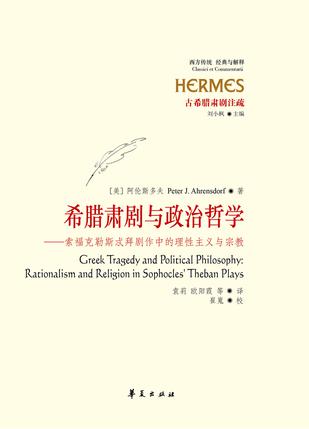
希腊肃剧与政治哲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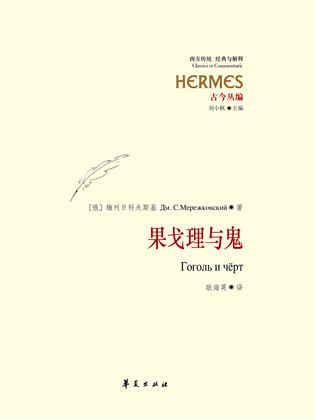
果戈理与鬼
《果戈理与鬼》揭示果戈理作品的神秘本质,揭示其作品中的魔鬼形象,亦即揭示最神秘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发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现实的人)和“主人公”之间完全没有界限,他在两者之间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被揭示的各种实体的“鬼”(赫列斯塔科夫,反基督一乞乞科夫,《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鬼),与其说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如说就是作者果戈理本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些都当做事实来接受:果戈理从自己身上写出了赫列斯塔科夫,一风儿吹透的果戈理的外衣启发了他的小说《外套》的构思等等。因此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和“主人公”常常是游移互串的。 《果戈理与鬼》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人写另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没有人比梅列日科夫斯基做得更好了。其独特的内涵与视角,精辟而深刻的分析,深深吸引了我们;因为他,我们真正地为自己事]开了果戈理。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的批评著作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看作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把他的作品只看作忠实地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国的现实。这也正是别尔嘉耶夫N指出的“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性”,即他的象征性、神秘性和宗教性。 -

赫尔墨斯的计谋
真实作为历史的基础我们应该了解 ; 篇幸布局与行文明晰作为手法应该通俗易懂。一个是肌体, 另一个是肌体的健康。 ——德莱顿《普卢塔克传》 当我专注于哲学与城邦之间的张力 , 也就是专注于政治哲学的至高主题时 , 就进一步确定了这种想法。至高形式的、或海德格尔式的当代哲学 与古典哲学的区别, 是由当代哲学的历史特性塑造出来的 , 以所谓的历史意识为先决条件 , 因此必须了解这种意识多少有些隐私、的根源。 ——斯特劳斯《剖白》 “不死”是一种用以表达灵魂与存在之原初联系的方法。要是你同意 , 它 表达着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心智思考永恒之物的能力。苏格拉底在某个地方说 , 正是诸神对存在的接近使他们像神:正是人 (man) 对存在的接近(但,又是一种为“遗忘”所败坏的“跌落了的”接近)使他成为人 (human):诸如此类都可以通过这种说法未表达: 灵魂是“不死的”。 ——葛利斯沃德 对话的意义在于努力重新认识理式,灵魂的意义在于自己运动,理性的意义在于推动灵魂,还有自我认识那镜照和肌的本性之意义,依据认错诗(《斐德若》中苏格拉底为悔过而作的第二篇赋——编者注),这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葛利斯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