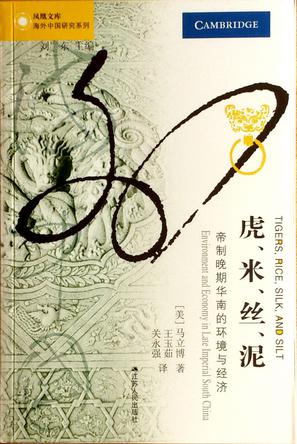故纸寒香
梁基永
《故纸寒香》是青年收藏家、广东文献研究者梁基永的又一力作,其中包括《款红》、《枫园忆凤》等25篇文章。其文字简洁雅致、严谨考究。字里行间透露了作者对古籍、碑帖等历史物件的极度热爱,又从侧面反映了作者作为一名收藏家独特而精准的眼光。阅罢《故纸寒香》,在作者的细致分析解读下,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遗世独立的历史陈旧感,又能感受到古籍等历史物件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力量。
买书买画,犹豫的总是那“一时之痛”,往往像容忍自家小孩的顽皮一般,一霎苦恼过去,迎来的喜悦必定加倍补偿。就如现在灯下翻阅,暖红的词句,慢慢流入心目,其愉悦又何可以言语形容。
序言
买书者言(代序)
读小学五六年级那时候,街上还没有什么杂志书刊,偶尔能买到一本《故事会》,都能从头到尾在课堂上偷偷看。有一回看到这么一个细节:土改时期某天,有两夫妇在看管地主家的房子,老婆说了句什么话,逗得老公很高兴,解下系在裤腰带上的钥匙:去,到楼上去,拿一盒子书,咱今晚做饭。
故事的题目、情节、人物,通通忘记了,可是这个细节,记在我“深深的脑海里”。老公是让老婆到楼上拿一函的线装书,去烧了做饭。江南和北方,收藏旧线装书一般都在二层,取其可以避暑湿之气,这小说的作者,必定亲身经历或者见闻过这种烧书作炊的事情。
“土改”大概是近代古书所遭受的大劫难之一,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态被彻底铲除,深藏于书房中的大量古书,被视作最不值钱的浮财分掉。稍后的“文革”不消说了。友人邢君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1967年他在广州做宣传干事,卷烟是稀罕物,能买到的只有烟丝。有一天工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函的宋版书,他见了问,这种“四旧”,拿来干嘛。工友高兴地说,你摸摸这纸多软,正好卷烟,于是他们七手八脚将书的天头地脚裁下来,欢快地享用了一周的宋代烟云。
中国曾经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鬼神晚上为之痛哭,这个传说大概是告诉读者,文字的破坏力有多厉害。明清时期,各地的文昌庙里面,都有惜字炉,带有字的纸要放到炉子里面才能烧掉。小时候我家的老保姆决不让我和弟弟践踏有字的纸,每当见到报纸什么的丢在地下,她会弯下弓得厉害的腰去捡起来,这种熟悉的情景让我至今不忘。
然而烧书这种事情,从帝秦到近代,反复地在这个崇拜文字的地方上演。书本身精美与否,大概和焚烧无关,甚至书里面讲什么,都不重要。赢政说种树书和占卜书可以留下,对于“土改”时期的贫农夫妇,种树书与唐诗的做饭效果是一样的。秦人一炬,火种绵延两千年而不灭.幸好中国的书也实在多,这是我们崇拜文字的结果。
二十年来,从地摊上五元十元的淘明清旧书,到现在拍卖场上锦衣镶玉的举牌争夺,旧书成了奢侈品,折射出国人对于旧书的感情变化。堪舆家说,人固有祸福兴衰,书又何尝不有否泰。今日的旧书价,大概是帝秦以来最高的时代,然而买书又读书者有几人哉。书应读的不止是书上的文字故事,书后面还有“人”,书交上了泰运,书里面的人,却可能还在史海中沉沦。
我的买书挑书,不专选刻划精美,不挑宋元佳椠,要说有什么专题,我只选有趣有掌故的买。近年不时有不少读者问我如何在旧书中捡漏、淘金,我只是回答,淘书看的是乐趣,看到书里面我喜欢的人、感动的故事,那就是我捡的漏、我淘的金。问者或会茫然,我则更加偷着乐:书画古玩,已经给好事者争抢到我们买不起的田地了,您就留着书这一亩三分地,给我们读书人种点残存的蔓草如何?
文摘
欵红
灯下读书,偶尔翻到前后的墨书题跋,仿佛重晤故人,尤其是那些音容不再的师友。对庐诗翁今夏仙游,他是给我题书最多的老辈诗人。我的喜欢请人在自认为善本上题诗,曾经被书友所刺,说唐突古书。然而我选的都是旧书的空白扉页,请写的也不算俗手,古人倘有知,恐怕亦不会深罪吧。对翁题书,从来都是写七言绝律。唯一的一回,他填了一首小令《忆秦娥》,交还给我时,再三摩挲着书衣,说:“我这次不客气,拿去复印了一册,词写得好,写得真好。”
是梁鼎芬的《欵红词》红印本,版心小,开本宽大,字体方正舒服。按照现在旧书通行的规矩,集部比经史贵,词集又比诗集稀罕,红印的词集,当然更加难得。在差不多十年前,旧书还没涨价,读书人能问津的时候,这书就价值一百元一叶,当时为了添置,还很踌躇了一番。买书买画,犹豫的总是那“一时之痛”,往往像容忍自家小孩的顽皮一般,一霎苦恼过去,迎来的喜悦必定加倍补偿。就如现在灯下翻阅,暖红的词句,慢慢流人心目,其愉悦又何可以言语形容。
我题写字幅送人,也常爱用梁鼎芬的诗词,题“家文忠公句”,文忠是辛亥后逊帝溥仪给梁鼎芬的谥号,有朋友便以为文忠公是我的族祖。其实他是番禺梁家,与吾家的祖籍南海不同。梁鼎芬的“番禺”,就是今天广州城东,他的舅舅张鼎华是翰林,自幼失怙的梁鼎芬受到舅家熏陶。对于经义制艺之类的科举门槛驾轻就熟。他成进士那年才二十一岁,入了翰林,还是钻石王老五。按照清代规矩,新科翰林未成家者,可以先不入史馆,请旨准假回家完婚。历史上皇帝是从来不管新科进士婚姻的,只有这种情况属特例,戏曲小说里面经常说“奉旨完婚”,所指即此。古代人成婚早,中进士而未成家者稀如晨星,梁鼎芬的早年运真是好到家了.
《歇红词》一卷,就是梁鼎芬在他一生最得意的这段玉堂金马时光所写。诗才高妙,名列“岭南近代四家”之首,梁鼎芬的词却只在早年写下这几十首而已。我常觉得古人的诗词集,取名都很见才思,然而诗集的名字又不如词集那么深婉曲妙,像梁鼎芬为自己的词取的“欵红”两字就极有味道。欵是挽留,红是春花,是落花,对着落花,文人便不免生出无可奈何的惋惜,大概就是欵红的含义吧。
梁鼎芬的学词,是在北京的翰林院学习时,住在番禺名士叶衍兰的家中,与叶家的子侄辈一起唱和的。叶衍兰祖籍浙江,先代落籍番禺,家中筑有南雪堂,藏有法书名画,铜器善本,本身又是翰林出身,是京城有名的学者和诗词家。叶衍兰住的宣南米市胡同,是广州人在京城聚集的中心区,梁鼎芬就寄居在彼,跟随前辈学词,居然日有进境,他对于自己的诗很矜持,自视颇高,然而词却随风扬弃,在生前也没有刊印成集。叶衍兰的孙子——叶恭绰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回广东时,偶尔在世叔处见到《欵红词》的一册抄本,叶恭绰早就折服梁的文辞,再看到里面有很多与自己父叔辈的唱和作,遂力任刊刻之责,才使文忠词留在天壤之间。
《欵红词》所收,都是在北京所写,“缠绵馨烈”,是叶恭绰形容得很形象的特点。少年得志的诗人,每日与名士周旋,游冶之处是都下胜境,偶尔又留点风流惆怅,笔下的情致不免缠绵,酝酿多了便趋馨烈。他写了几十首的《浣溪沙》,集中只收了一部分:
儿女神仙反自嫌,半生幽恨在眉尖,相思极尽转庄严。
春景写时三二月,花枝障碍几重帘,缠绵蕉萃一时兼。
蕉萃就是憔悴,缠绵与憔悴,一时都来眼底,这是热恋开始时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儿女神仙,简直就是梁氏与情人的写照了。
光绪十一年,梁鼎芬二十七岁,本该是扶摇直上的年纪,他却选择了上奏章弹劾当朝大学士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其结果比他预想之中还惨重,他被慈禧训斥为“妄劾”,连降五级处分,逐出都门。关于梁鼎芬的这次大胆行动,固然是他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然而也有传是因为他笃信广东同乡前辈李文田的劝告,断其相中有血光,只能弹劾大臣以消灾。他当时的心境究竟如何,是如释重负,是满怀悲抑?在慈禧下旨严谴的第三天,他和挚友文廷式到南河泡赏荷花,填了一首《蝶恋花》:
忆昔荷香香雾里,绝好花时,已是伤秋地。泼水野凫随棹起,满衣湿气沾凉翠。
独写新词君有意,补画题诗,重省当时事。欲说情怀无一字,鼓琴莫待钟期死。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翰林到奉旨严谴要收拾行囊,他还有闲情去赏荷花写词,也许他真信李文田的罢官避难之说。只有结句“鼓琴莫待钟期死”,隐隐透露了他心目中那一丝灰涩,犹如秋后荷花池上掠过的湿气。
从离开京城,到湖北张之洞幕下教书讲学,再接近三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京师,梁鼎芬已经是双鬓带霜的中年汉子。昔日出都城时,他将爱妻龚氏托付文廷式,妻子却从此就跟文相好,见了梁鼎芬也只是“行宾主之礼”,昔年笔下的儿女神仙从此是路人。、梁鼎芬的回到北京,是张之洞一力保举,可惜其狂狷之气不但不改,且不减当年弹劾李鸿章之勇,又再次弹劾当国的庆王奕勖与袁世凯,被慈禧再一次逐出京城。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