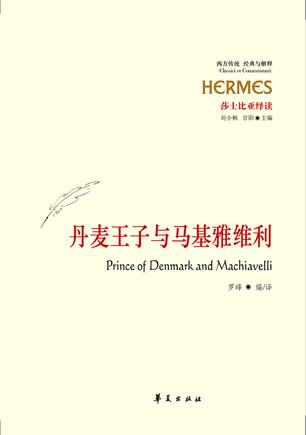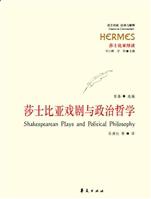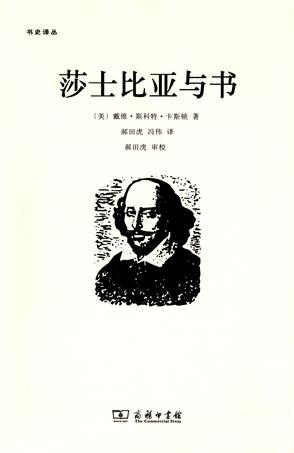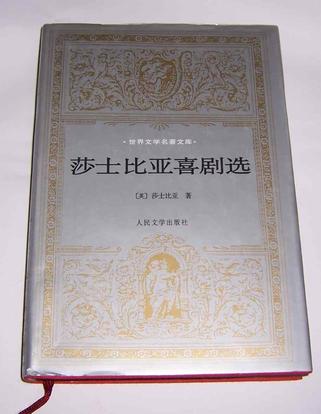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
彭磊 选编
在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研究文献中,本书辑译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解读莎剧的文章。因为“政治哲学对于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诗原本就是传达政治哲学教诲的最佳形式。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以及更古老的时代,“诗的内容和效用之获得意义,源于诗人政治上的高贵性。诗不是自为的,它只有依系于那些激励最优秀的行动者的目标,才会获得生命”;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戏剧)表达了对政治事物的关切,并揭示了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
莎士比亚借由浪漫主义而成为“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亦借由莎士比亚发扬光大, 浪漫主义所塑造的莎士比亚如今仍然深深支配着我们的理解。 本书编者认为,要看清莎士比亚的真正面目,还应有一个视角和途径,这就是政治哲学,通过这条路径,我们能看清原初意义上的诗,能辨识出莎士比亚与浪漫派的不同:浪漫的抑或政治的莎士比 亚,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抉择。
本书的视角独特,想必会给人们许多新的启示。
编者前言
如书名所示,这里所辑译的文章大多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解读莎剧。在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研究文献中,突然冒出一类“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没什么好稀奇——毕竟我们早已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花哨,听到过许多时髦的新名词。
也许,这一“花哨”与其他都不同呢?说到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得追溯到五十年前:1964年,布鲁姆和雅法合撰的《莎士比亚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出版。布鲁姆在序言“政治哲学与诗”中强调,“政治哲学对于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诗原本就是传达政治哲学教诲的最佳形式,只不过,现代人将诗与政治更进而与哲学分离开来,追求纯粹之诗或纯粹之哲学,遗忘了中间那片纷杂变幻的政治之域。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以及更古老的时代,“诗的内容和效用之获得意义,源于诗人政治上的高贵性。诗不是自为的,它只有依系于那些激励最优秀的行动者的目标,才会获得生命”;现代人则认为,“诗超越了对政治的基本公共关怀,艺术家更近乎反政治的波西米亚人,而不是心系政治的贤人”——不错,如今只要哪位“艺术家”受到监禁或流亡,立刻就会被奉为充满自由精神的大师而广受追捧。正是这种现代诗学使我们看不到,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戏剧)表达了对政治事物的关切,并揭示了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不过,这一现代诗学观念拜谁所赐呢?布鲁姆说:
自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来,人们对诗的性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如果还把诗看作是自然之镜,或把诗解释成实际在教导什么,如今会被视作对艺术圣殿的亵渎。人们相信诗人们没有什么意图,诗人们的史诗和戏剧自成一体(sui generis),不应由政治社会或宗教的标准来评判。由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认为仅仅是文学作品,它们便与激发行动者生活的那些重要问题毫不相干。
浪漫主义处在思想史上的什么位置?它是卢梭的子嗣,施特劳斯曾称它“比任何一种形式的古典主义都更明显地是现代的”。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浪漫主义明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布鲁姆和雅法这两位政治学教授来研究莎士比亚,绝不仅仅出于对文学的兴趣,而是出于通古今之变的问题意识:既然浪漫主义如此现代,就值得对浪漫主义的诗乃至浪漫主义所塑造的莎士比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要回到古典的诗乃至古典的政治哲学,莎士比亚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节点,因为莎士比亚与浪漫主义有着莫大的关联。
浪漫主义对莎士比亚的神格化是莎剧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一章。[1] 大施勒格尔(A. W. Schlegel)用德语翻译了17部莎剧,小施勒格尔(F. Schlegel)径直宣称“莎士比亚的诗完全是浪漫性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总汇性如同是浪漫艺术的核心”;[2] 歌德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献给莎士比亚,并把《哈姆雷特》搬进这部成长小说,让主人公解说哈姆雷特的性格;[3] 雨果认为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诗的最高形式(即戏剧)的最高顶点,柯勒律治则给我们留下了两大卷莎评。[4] 这些浪漫派巨头以不同的方式对莎士比亚顶礼膜拜,使莎士比亚的声名越出英伦,远播四海。但是,这一切只因他们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了浪漫主义的诸种美学原则:天才、想象力、情感、自由、个体、疯狂……尽管莎士比亚戏剧饱含政治哲学义涵,现代的浪漫诗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只见到美的流溢——小施莱格尔云:“所谓美,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快感的对象,完全独立于需求和法则的强制之外……现代诗的终极目的只能是最高的美而不会是别的,即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美的完善”,而“所有现代作家中,是莎士比亚最完美、最准确地刻画了现代诗的精神”。[5]
莎士比亚借由浪漫主义而成为“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亦借由莎士比亚发扬光大,[6] 浪漫主义所塑造的莎士比亚如今仍然深深支配着我们的理解。布鲁姆生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再次探讨莎剧,相关内容其后以《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为题抽出来单独出版(Shakespeare on Love and Friendship,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年),序言中说:“莎士比亚能登上如今这般不可置疑的高度,多赖于浪漫派的关系。但是,浪漫派的插手败坏了莎士比亚,而浪漫派自己却扎下了牢固的根基。”
我们如何才能看清莎士比亚的真实面容呢?也许,政治哲学便是一条路,通过这条路,我们能看清原初意义上的诗,能辨识出莎士比亚与浪漫派的不同:浪漫的抑或政治的莎士比亚,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抉择。自布鲁姆等人导夫先路以来,政治哲学学刊《解释》(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上便不断刊载研读莎剧的妙文。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选自此刊。三年前,刘小枫老师把文章交给内子翻译,后又嘱我编辑此书,而今书成,只觉字里行间布满了时光的影子。
译者在翻译时或参照朱生豪先生译本,或参照方平先生主持的诗行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非特别注明外,均据方平本,特此说明。
彭磊
2010年12月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 浪漫派的莎评文献汇编,见Jonathan Bate,The Romantics on Shakespeare,London:Penguin,1992。相关中译可参《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与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64年,以及《莎剧解读》,张可、元化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九册,前揭,页99-100;《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页247,另见页71:“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总汇性(Universalität)是施勒格尔核心的诗学观念。
[3] 莎士比亚之名即是威廉,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似乎可以译成“大师莎士比亚”。
[4] Coleridge’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2 vols.,Thomas M. Raysor编,London:Constable,1960。
[5]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前揭,页22,20。引文有所改动。
[6] 就笔者所见,两部介绍浪漫主义的文集均辟专章讨论莎士比亚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参见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Michael Ferber编,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5,页29-48;A Companion to Romanticism,Duncan Wu编,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7,页51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