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疑古时代
《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先生,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1992年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以来,走出疑古已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是作者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质量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六篇,第一篇论古代文明,第二篇神秘的古玉,第三篇新近考古发现,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第六篇续见新知。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主题。 李学勤先生的名著《走出疑古时代》初版于1995年,1997年又出了修订本,均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又由长春出版社出了新版(2007年1月)。如李先生在初版《自序》中所说,该书是其“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而且所及范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汉代初年”。后面两个版本与初版相比,只是增加了《续见新知》一编,收入初版之后李先生新作的十来篇相关的短文,并校正、修改了初版中的“一些错误之处”。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1992年针对中国近代乃至古代“疑古”思潮提出的一个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又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走出疑古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而且“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入必读书目”(新版《出版说明》)。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这篇号角性的著名演讲,可谓恰逢其时。该文“编者按”强调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995年,李学勤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走出疑古时代》被作为导论置于书首,并即以此为全书题名。 本书1995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等撰有书评,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院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为必读书目。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1997年,此书再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作者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和思想界。 -

世界通史(共3册)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把全世界作一个统一体来写的世界通史。上起初民时代,下迄“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采取东西方各个历史阶段对比的方法,写出了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脉络,而不是东西方各国别史的拼合。本书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现象,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多所涉及,而绝无教条主义。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外国的、中国的材料(许多是原始材料),对前人的学说、观点、也择其重要者加以介绍或评论,言之有据。本书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其传世的历史价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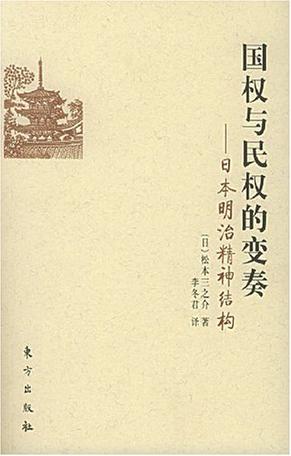
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轨迹是一椭圆,它围绕国家主义和欧化主义这两个中心作向心运动。国家主义根柢于儒家精神,欧化主义则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但它却启迪了日本明治时代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将这些互相对立的主义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统一的精神结构,并推动它们向极端发展。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主义导致军国化,欧化主义导致全盘西化。作者站在当代市民社会的立场,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反思,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

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本书收录了陈垣先生1947年9月至1949年6月在辅仁大学讲授“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法”课的教学日记和札记,以及李瑚先生的听讲笔记。取清儒史学考证之书,注重实习,因其所考证者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使后学者得正确的读史之法、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当时这两门课都以《日知录》为教材,内容可与陈垣《日知录校注》一书相互印证,互相补充。 -

突厥集史(全二册)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

裂变中的传承
清季民初之时,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的传统送进博物馆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