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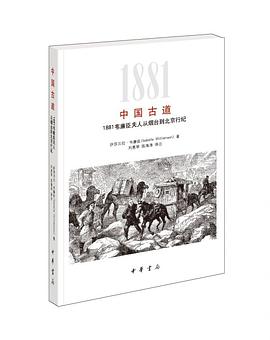
中国古道
本书是近代著名传教士威廉臣的夫人所著,记录了其1881年随威廉臣从烟台到北京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展现了一幅在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作者随丈夫在中国生活多年,能熟练使用中文,交际广泛、处世圆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协助韦廉臣之余,她用自己独特的西方女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力,书写中国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社会的世态风俗,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忆。
本书中,作者从西方女性的视角出发,在记录大量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的同时,笔墨间洋溢着初次接触异域风土时的好奇和喜悦。同时,因为作者的女性的身份,使得她可以深度接触中国的女性,得以见识并记录那个时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原态,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丰满的近代社会生活史资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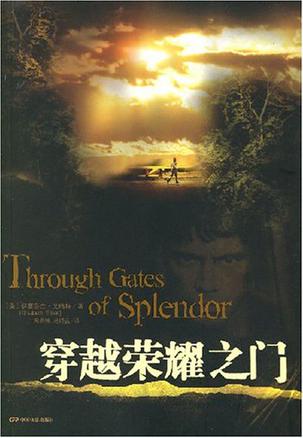
穿越荣耀之门
内容简介: 1956年,五名立志将福音传播到丛林深处的传教士,放弃了舒适安宁的生活,冒险深入厄瓜多尔原始丛林,希望向印第安土著部落奥卡人宣讲福音。不幸的是,他们刚踏上部落的领地,就遇难身亡。尽管他们手中有枪,却始终未扣动扳机…… 从不欢迎外来者的奥卡人,起初并没有拒绝传教士的礼物和友好。经过无数次试探性接触后,五位传教士觉得机会成熟,决定于1956年1月的某天,准备与奥卡人进行一次关键性会面…… 五位年轻人的妻子不约而同地屏息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 《穿越荣耀之门》评论 这本书应该被每一个基督徒的图书室收藏,它使我们看见那些致力于福音使命的家庭,是怎样给出了一个“标竿人生”的定义。 ——亚马逊读者 评论节选 这本书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真实地信靠上帝究竟能有多少? 如果我们被呼召,我愿意放弃些什么? 我会牺牲我所喜欢的舒适生活吗? 我会牺牲自己计划好的人生吗? 比牺牲自己这些更难的,是如何面对我们的妻子或丈夫。我愿意冒着牺牲他/她的危险,开始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旅程吗?甚至我们永远都不能再见面,直等到天堂相会的日子? 本书将这样的信仰历程,属灵的挣扎,神的作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激励。 ——亚马逊读者 评论节选 《穿越荣耀之门》评论 尾声一 1958年11月 从那个星期天下午到今天,将近三年过去了。此刻,我正坐在棕榈滩西南方不远处的提瓦努河畔的一间小茅屋里。在三米开外的另一间茅屋里,坐着杀害我丈夫的七人中的两个。其中一人叫吉基塔,他刚给三岁半的瓦莱丽烤了一只大蕉。为了喂饱在这块空地上居住的十来个奥卡人,吉基塔的两个儿子扛着制作精巧的吹箭筒到丛林里打猎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只有那位能让斧头漂起来,能让日头停下来,能将活物的气息掌握在手中的全能的、永远的上帝才办得到。 五位传教士死后,宣教飞行团契继续给奥卡人空投礼物。他们依然友好地接受,但我们知道再也不能以此判断他们的态度了。 飞行员纳特的姐姐雷切尔·赛因特依然在黛玉玛的帮助下潜心研究奥卡语。黛玉玛与其他几千印第安人一起,渐渐认识主耶稣,并开始祈祷,让上帝光照她的部落。 1957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阿拉胡诺麦卡利一家原来的工作站里,突然来了两个克丘亚人。他们从库拉赖河赶来告诉我们,有两个奥卡妇女在他们家里。我立即跟他们走,在搜救队曾住过一夜的克丘亚人居住地,见到了曼卡姆和明塔卡。明塔卡是曾到“棕榈滩”与传教士见面的两个女人中较年长的一位。 后来,这两位妇女与我一起回到了山地亚。我开始在那里跟她们学语言,并不断祈求上帝领我们进入她们的部落。上帝最初的回答出现在《尼希米记》九章19节和24节的应许中:“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伏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 当雷切尔和黛玉玛从美国访问归来后,我们去看望她们。这三位奥卡妇女在分别十二年之后,再次见面了。她们打算携手重返部落。1958年9月3日,她们回去,让族人明白了那些友善的外人是带着爱来到丛林的。三个星期以后,她们又回到阿拉胡诺,玛吉·赛因特和我一直在那里等着。她们又带来了七名奥卡人,还邀请我和雷切尔去部落里与族人一起生活。 于是,我们在1958年10月8日来到奥卡部落。期待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奥卡人很友好,且乐于助人,待我们像亲姐妹一样。不但帮我们盖房子,还把肉和树薯分给我们吃。他们说,杀死传教士只是因为错把他们当成了食人者,当初下手的根本原因是恐惧,现在他们后悔了。 但是我们知道,那并非意外。上帝总是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来自很多国家的信件提到,上帝借五位传教士的经历影响了成百上千的人,因为他们坚信“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因此,我们请求那些为我们祈祷的人继续祈祷。虽然我们进入了这个部落,但也不要忘记这仅仅是个开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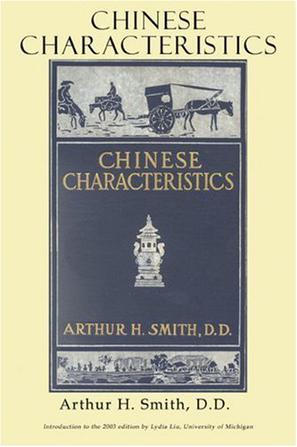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 was the most widely read American work on China until Pearl Buck’s The Good Earth (1931). It was the first to take up the task of analyz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scientific" social and racial theory. Written as a series of pungent and sometimes comic essays for a Shanghai newspaper in the late 1880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among the five most read books on China among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as late as World War I and it was read by Americans at home as a wise and authentic handbook. The book was quickly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just as quickly into Chinese. It was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 and has maintained its authoritative status for over a century — as the quintessential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race drawn by a Westerner. Lu Xun, the most prominent Chinese cultural crit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rged his students to study and ponder Smith’s message, which was very widely debated in Chinese student circles. Within the last decade (the 1990s), two different, new translations of Smith’s book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and both editions have enjoyed wide distribution and readership.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since World War II,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widely quoted (though seldom read) as an example of Sino-myopia and Orientalism. Despite such Western pseudo-intellectual bias, Smith’s arguments retain the power to provoke critical introspection among Chinese and, for the honest, among Westerners as wel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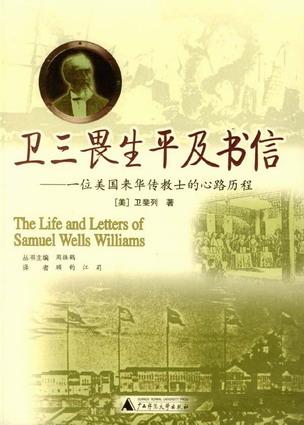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这套丛书具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这套丛书具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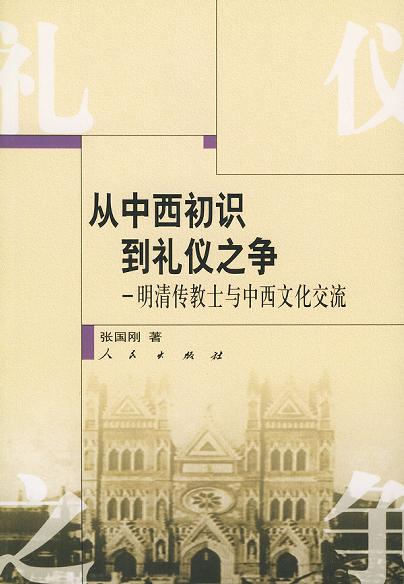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形态。其中,后面几种文明在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曾经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唯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因此,以大航海时代为契机的中西初识,才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内容。礼仪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在远东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使“异端”或那些还处在泛灵主义或图腾崇拜的“野蛮人”皈依,而是要面对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她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文化反思。,无论是利玛窦的调和策略,还是索隐派对中,国经典密码的解读,或者是耶稣会士反对派的攻讦,都折射出西方文明面对传统中国的独特文化韵味所发生的认同危机。这个问题的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礼仪(术语问题、祭祀问题)的范畴。 我们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中国语言问题。《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说:上帝造人时,人类都讲同一种语盲。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其遗址据说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城塔,以显示人类的力量,所建造的塔直指云霄,被称为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可怕,于是使用法力把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以阻止其互相沟通o《创世记》属于《摩西五书》之一,是犹太教最早确立的圣书正典,一般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由四种不同的底本资料缀合而成。大约比希罗多德的《历史》要晚一百年左右。其实寻找初民语言的故事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早。希罗多德就讲过古代埃及法老寻找初民语言的一个实验。一位名字叫撒姆提齐(Psammetich)的古埃及后期的一位法老相信,新生婴儿之间如果不受当代人的语言影响而互相说话,那么他们嘴里讲出来的一定是上帝所教给的初民语言。于是,法老下令把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婴儿与其母亲隔离开来,交由牧羊人独自护养,任何人不得与婴儿说话,否则被处以极刑。两年以后,到了孩子该说话的年龄,法老下令停止给孪生婴儿喂食,他相信饥饿将迫使婴儿开口,说出来的就将是人类最初的语言。结果,观察者向法老报告说,婴儿说出的词汇很像斯科特语中的“面包”。法老大喜,宣布斯科特语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十三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被试婴孩不幸死去。在《圣经》知识主宰的世界里,寻找初民语言长期以来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十六世纪以后的一们艮长的时间里,当欧洲人接触到中文的时候,关于中文起源于什么,是否上帝所造的初民语言,是否具有理性的逻辑语言、哲学语言这些问题曾经是欧洲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又比如中国历史纪牢问题。从门多萨、曾德昭,到卫匡国、柏应理,中国编年史知识陆续传播到欧洲。十七世纪欧洲学者对此的最大困惑是,它居然比《圣经》里的历史还要古老!于是,围绕着中国上古历史是否有悖于《圣经》的编年学问题便闹得沸沸扬扬。耶稣会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古史体系引起了西方教俗世界对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同危机,其震动可想而知。有人怀疑它,有人拒绝它,也有人接受它。当时已经有学者勇敢地利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提出“亚当之前人类说”的假设。当然主要的观点还是在调和中国古史与《圣经》体系的矛盾。有学者采用《七十子译本圣经》来讨论诸如“世界的寿命”这样的问题。因为《七十子译本》可以将迦勒底人、埃及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与《圣经》的年代体系调和起来。此外,还有孔子道德哲学的问题,在十七~十八世纪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中国道德哲学也引起莱布尼茨、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时代旗手的纵情欢呼。 总之,通过晚明到清前期三百年间(1500-1800)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 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仍然有持久的影响。 如果着眼于“传播”这个环节而暂时不考虑传播的后果,那么十六-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可以被看作一部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交流史,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传教士以及来华商人和使节这些辅助渠道。 这个时期的中西交往是伴随欧洲征服世界的进程而展开,但中欧间也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交往,没有牵扯主权与政治利益,欧洲人的殖民者形象在中国沿海尚未有清晰表现。欧洲的商船和战舰远航各地,也到了中国海岸,未知中国虚实的西方战舰不敢贸然侵扰中国,此时的欧洲人慑于中国多年前已流传出去的盛名而只希望和平地与中国开展贸易,并屡屡派遣使团想要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但基本上可以说一事无成。中国人对远洋外夷明显缺乏兴趣,只是据守自己的海岸和几个港口与欧洲商人和各朝贡国商人进行一年一度的贸易,多少怀着恩赐的心态懒洋洋看他们运走一船船丝绸、茶叶、瓷器、漆器。中国商人与港口官员面对这些语言、服饰、相貌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欧洲人,除了例行公务之外,也许并没有被激发起多少求知欲。相反,来华的欧洲使节们对中国的山河草木、风土人情却兴致盎然,在来去京城的旅途中记录下许多见闻与评论,结果成了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重新撩拨欧洲人对中国生发浪漫情怀和无限遐想的触媒。就连那些没到过中国而只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的欧洲旅行家,也忙不迭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中国印象纷纷呈现给欧洲读者,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满足足迹未至东方的同胞们的好奇心。推波助澜的是一船又一船在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上岸的瓷器、丝绸、漆器、茶叶等中国商品,它们展示出一个可看、可摸、可以感觉和品尝的光彩眩目、缤纷绮丽的中国。就这样,中国的美丽富饶和强大在十六世纪已经深入欧洲人的心,而且传闻中这还是个文化发达的国度。十六世纪末博学而又受人尊敬的耶稣会士进驻中国,然后向欧洲同胞宣布,他们可以见证中国的确文明昌盛。从此,他们在一个因物质文明发达而令欧洲大众目迷五色的中国形象之上又推出一个令欧洲知识分子兴奋不已的拥有高水平精神文明的中国形象。 使节与商人的限制在于,他们无缘深人中国并长期居留,不懂中国语言也看不透中国文物。耶稣会士则以其非凡的创造精神克服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通过将天主教与孔子儒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附会而赢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承认,又通过对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定容忍而免除了自己被目为中国社会秩序及法律的反对者与破坏者的危险。于是在一个对外国人防范多于欢迎的时代里,他们成为唯一获官方许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以及他们主动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不仅使他们在中国赢得比其他宗教修会大得多的传教成果和势力范围,也使他们成为向欧洲全面和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亦即充当着晚明前清中西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 然而耶稣会士的活动几乎从头至尾被笼罩在礼仪之争的阴影中,他们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为他们带来莫大荣耀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礼仪之争这一沉重负担,所以这一段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交往也不得不深深烙刻下礼仪之争的痕迹。事实上,随着礼仪之争被禁,这段中西文化交往也便趋于停滞,到1775年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传到北京时,此次中西的直面接触已然了结。1793年10月,在华最后一位耶稣会士钱德明去世,象征性地落下了这场耶稣会士为主导的中欧交往的帷幕。差不多同时,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仅从时间上看,似又接续起中西交往的脉络,然而这实在已是一个性质有重大差别的新交往故事的序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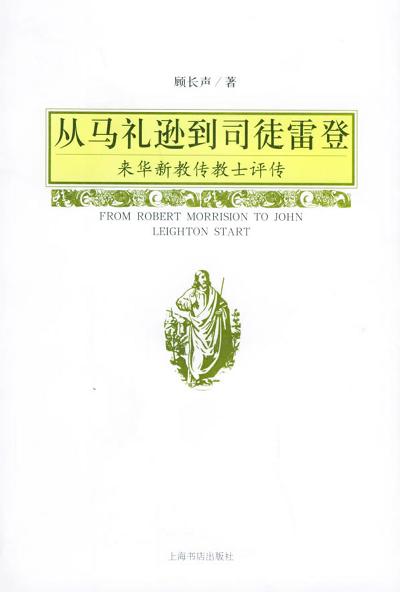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近代中国海禁重开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的接踵来华,成为晚清以及民国时代中外交往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事实上这个成分复杂的特殊群体的在华活动,涉及到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已远远超越传教范围。本书根据第一手资料,为其中最著名或在某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30多位人物分别立传,传中大量引述档案文献、书信日记,以及作者采访这些人物后裔亲属所得的口述史料,多系一般专书中罕见,从而为从事近代史学习和研究的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各专业学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